“Holy Shit,这意味着有200万人玩了我的游戏,谢谢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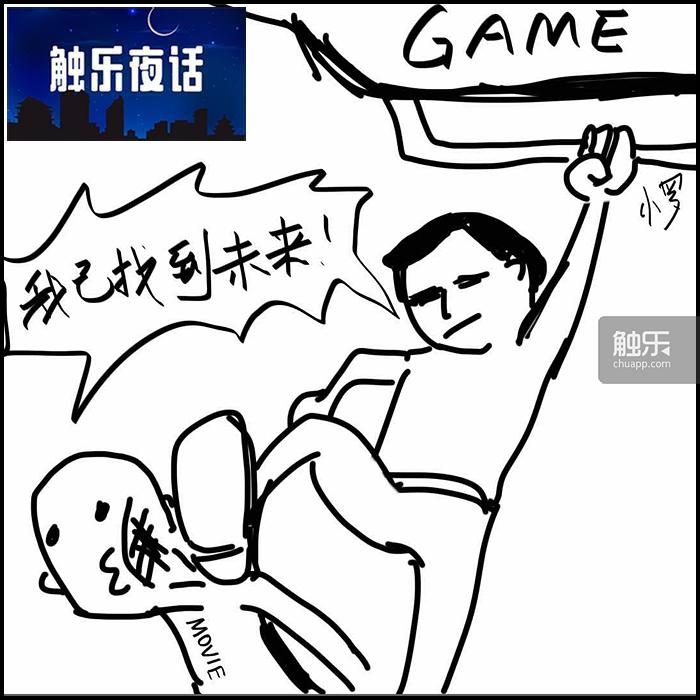
发售不满1个月的《A Way Out》卖了100万份,这意味着只能双人合作的这个独特设计赢得了市场的认可,Hazelight工作室14日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制作人Josef Fares转发时不忘爆了句粗口:“Holy Shit,这意味着有200万人玩了我的游戏,谢谢你们。”
多数人记得Josef,可能不是因为他的游戏,而是去年的TGA颁奖现场,他在台上的那段激情发言,他先是朝着奥斯卡竖起了中指,接着痛骂当下的游戏产业,还不忘揶揄一把发行方EA。这些疯狂的举动让人鼓掌叫好,也让人疑心他是否喝醉嗑药了。
最近IGN放出了一段长达一小时的专访视频,主持人一开始让Josef重看了这段视频,并问他当时的状态和现在的感想。这段采访呈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Josef,但最让我着迷的是,他身上那股看似源源不尽的激情与活力,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将采访的一些要点摘录如下:
重新观看TGA那段视频时,Josef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这就是我的样子,我从来不计划任何事情,我从不写剧本。”他解释道,“问题在于我大脑有时候想说这些,它们会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发泄出来。”
“整个去它的奥斯卡的事,是因为我之前听到……有人在讨论TGA像是游戏‘奥斯卡’,我就想去它的,这说起来很棒,去它的奥斯卡。“他接着说,“这不是说我有什么针对奥斯卡的地方……毕竟我不是个拍电影的。”
“我刚刚飞过来。可能才睡了两个小时左右,处于倒时差一团糟的状态。”
“我在活动前的确喝了啤酒,但没有一脸屎色或瘫如烂泥。”重新观看那段视频,Josef依旧觉得很好玩,也很喜欢,“我对(主持人) Geoff Keighley感到有点抱歉。但那的确是一段好时光,有时你就需要干它一发。”
面对“EA事后是否有过非难”的疑问,他否认后转向了激情澎湃的一面:“没人来教训我,我对自己做的东西有热情有信心……我会继续做下去而不用别人告诉我怎么做,我宁愿睡大街也不要做自己都不信的游戏。”

这种异样的激情贯穿于整个采访过程。你可以看到面对主持人的每一个问题,Josef总能在回答的基础上,莫名开始延伸并发散出去,变作一种情感上的极力抒发。这种抒发是“我对自己的游戏有信心”,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构想”,就像他在TGA上面对众人放出的那句狂言:“如果你把它从头玩到尾,你就不可能不喜欢它。”
这种蓬勃、向上的热劲儿,在他反复的宣称下,总让人疑心是一种盲目自大,以至于也有人觉得他疯了,但他的作品偏偏让你不得不信服,《兄弟:双子传说》销量百万,获奖无数;剑走偏锋的《A Way Out》,也在EA完全不看好其市场前景的前提下,赢得了玩家的认可。叫好又叫座的这两部作品,也让Josef有了这样的底气。
我不确定这种激情跟他的成长经历是否有关,他出生于黎巴嫩,后来搬去了瑞典,他目睹了战火纷飞、家破人亡的惨剧,这样的经历让他感受到“活在当下”这个词的意义。他在采访中回忆:“不是说这是好事或是坏事,它就有一种影响,逼迫你去珍惜当下。”这让他学会了痛痛快快地爱,痛痛快快地恨,痛痛快快地流泪或歌唱。
从小时候第一次接触雅达利开始,他就自觉地成为了一个硬核玩家,以至于他去别人家拜访,如果看到对方家里没有主机,他觉得就像是家里少了厕所,面对那些对从不玩游戏的人,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他会跟哥哥通宵达旦地玩游戏,他喜欢《超时空之钥》《最终幻想》之类的俯视角RPG,而这也成为后来的《兄弟:双子传说》最初的灵感来源。

尽管对游戏有着如此狂热的爱,但他最开始走上的是拍电影的路。他从朋友那借来摄像机拍了一系列短片,后来有制片公司看上了联系他做电影。他22岁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Jalla!Jalla!》在瑞典取得了非常优秀的票房成绩。
他喜欢斯蒂芬·斯比尔伯格、詹姆斯·卡梅隆,推崇斯坦利·库布里克,他喜欢电影,但面对影视媒体采访,他总爱大谈游戏,往往让记者一头雾水。

一位老友开了个学校,带学生去参加夏令营,开发游戏,为期6周,问他感不感兴趣,他当晚就有了想法:双手操控兄弟二人。在这位导师的帮助下,Josef从对做游戏一窍不通,慢慢进步,做了一个20分钟的Demo。他拿去给人看,大家都很喜欢,但没人对游戏的前景有信心,大家劝他,你毕竟是导演。
他身上的那股执拗劲起来了,他强迫自己组建团队开始制作,心想一定要做出来,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这中间自然经历了许多困难,这些他都在采访中一笔带过。最终《兄弟:双子传说》诞生了,人人似乎都喜欢这款游戏,不论是兄弟羁绊还是独特的操控,Josef借此在业界崭露头角。
为什么选择转行做游戏?
他反复对媒体强调,游戏有更多的可能,相比影视行业业已形成的制作规范,游戏还有很多潜力尚待开发,游戏所独有的交互体验也令他着迷,这是游戏才能实现的。他迫不及待想把头脑中的想法做出来,当初想到《兄弟:双子传说》的结尾时,“我当时兴奋得睡不着,觉得一定会让世人震惊” 。
在处女作大获成功后,很多厂商找上门来合作,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对游戏有100%的掌控权。我不清楚他与EA签订的协议具体细节,但按照他在采访中的说法,EA非但从中拿不到一分钱,也没法干涉创作的自由。尽管EA对纯双人的设计有过质疑,但最终拍板定夺的只能是他自己。
从镜头的调度、情感的推进,到节奏的把控,我们在他的游戏里可以看到很多影视的技巧。但令我觉得有些意外的是,当主持人问他从影视行业借鉴了哪些东西制作游戏时,Josef并没有认领这个假设。他说自己做游戏并不是要在向影视的方向上迈进,而是尽可能反向而行,去做不一样的东西。

对于身处游戏行业,Josef感到非常自豪。这个行业有许多尚待开垦的东西,他自己也有很多想要实现的想法,游戏可以做到的东西还远远不够。
有媒体特意挑出反对意见抛给他,电影批评家Roger Ebert曾称,游戏媒介不是一个确切的艺术形式。“他完全错了。”Josef驳斥,“我甚至不会跟那些人争论,因为那根本说不通,也完全蠢透了。”
他拿绘画举例。“如果你问:‘我给你画了幅画,你会将其视作艺术吗?’我想大多数人会说:‘是的。’我的回答是,画画还只是做游戏的一小部分呢。我想到一些概念艺术家的画……而这不过只是一小部分。”
“你知道的确有人会这样想——好比说,你知道他们会说:‘哦,这是计算机制作的。’就像是你觉得自己可以拿一台电脑直接敲出一个开放世界……然后直接按下确定键?人们总爱这么去想。”
“我甚至都不听这些东西。它们完全就是狗屎,”他显得有些愤怒,“这就像是对我说:‘Hey,我很蠢。你要跟我聊天吗?’我会回答:‘当然可以。让我们聊吧,但是聊点别的吧。’我根本就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认真。”
Josef讨厌业界的开放世界趋势,除了R星做出的典范(我猜他忘了提《旷野之息》)。他喜欢日本游戏,他难忘《超级马力欧银河2》,也在等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他还很好奇宫本茂会不会生气,因为他看上去时刻都笑眯眯。在推动游戏产业发展上,这些人有着卓越贡献,他也想做出自己的努力。
现在,制作了3年半的《A Way Out》已经告一段落,“我对后续不感兴趣,对过程更着迷。现在它已经结束了,我将开始下一个项目。”就在4月5日,Josef宣布已经开始了下一款游戏的制作。
他在采访中承诺会推出几款游戏,因为自己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将彻底离开影视行业,未来也有可能再度回去拍电影,但谁也没法猜到这个看似疯狂的大脑,究竟会讲出什么样的故事。

这种仿佛燃不尽的激情,究竟是由什么在支撑它,看完IGN整段采访视频,我依旧没能找到答案。
人们很容易被他疯狂的外表、泛滥的说辞、旺盛的热情所感召,但若深究下来,你会发现在这背后同样有着缜密而深入的思索。Josef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信心,也热情,敢于去尝试,并全身心投入,不论是拍电影,还是做游戏。
创意往往伴随着风险,Josef深知这一点,但他并不害怕,反而跃跃欲试,即使最终以失败告终,他说自己需要思考的,不过是怎么睡大街而已。
《A Way Out》的背后只有一个十几人的团队,现在达成100万的销量,无疑是对Josef这种狂热的最好嘉奖。投入其中,做些不一样的东西,收获认可,尽管这个模式可能不是业界的常态,但Josef的例子多少还是让人备受鼓舞。
游戏产业需要这样的人,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