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那个女孩玩起了游戏。

读者朋友们,当你们看到这篇夜话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登上了出差的班机。就像陈老师不久前说的那样,在坐飞机出差时想象自己在进行开高达模拟训练,就会好过很多。飞行的目的地是上海,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个和上海有关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准确地来说,是一个网友。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我们通过网络认识,在微信上聊了很久。她在上海工作,刚好那时候我在上海有一次雅思考试,也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古怪想法,我们决定在这座城市的街头见上一面。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我们都是很不一样的人。她当时做的是销售岗位,每天妆容精致漂亮,而我是个如假包换的阿宅,对粉底、口红、眼影等东西没有一丁点天赋。她朋友很多,走到哪里都有人陪,而我那时候冷漠又自闭,不仅没人性,而且死傲娇。
但我们的关系出乎意料地好。她挺热衷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细节,讲起话来几乎没有停下的时候,在最热切的时候,因为我整天戳手机聊天,我的舍友几乎误以为我脱单成功。
她对电子游戏、机器人、宇宙与生命的最终奥秘缺乏兴趣,从没听说过乔治·奥威尔、豪尔赫·博尔赫斯或是刘勰、钟嵘(后来在我的反复理论轰炸下她去读了《动物庄园》)……总之,多年前的我就是个中二病晚期患者,她觉得我喜欢的东西相当古怪,我本人则是个“无趣的家伙”,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频繁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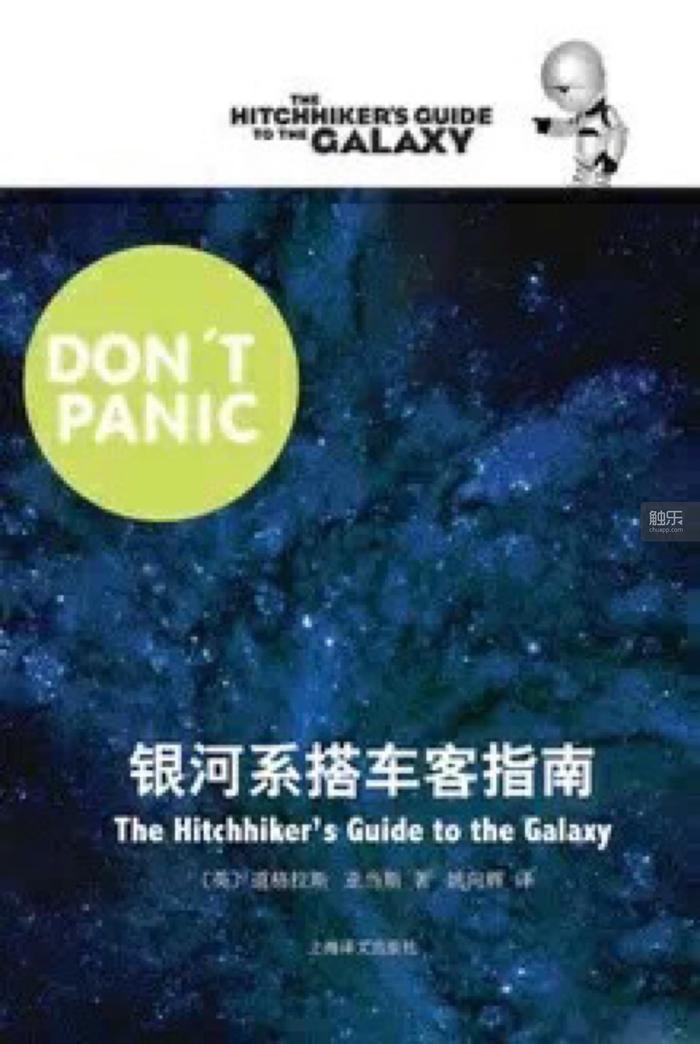
上海的那个晚上,当我坐在她面前,在现实中看见我的网友的时候,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畏惧。我并不是一个缺少胆量的人,曾经在恐怖游戏中追着怪物连砍一条街,也在几千人的礼堂中做过代表发言,我没有理由——这没有道理,我会在一个妆容精致的同龄女孩面前怕得发抖。
她是我的天敌。
我跟她说过的秘密太多了,多到我难以抑制地觉得害怕。我在她面前的样子,和我在其他所有人面前的都不一样,很难说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我不太清楚她是不是能够领会我曾经说出的那些句子的真实含义——我曾以为我永远不会和她见面,因此遣词造句从来毫无顾忌。
她觉得我会喜欢厚切牛排,煎得一面流黄的太阳蛋,端着红酒在放着高雅音乐的西餐厅里和人碰杯。但我事实上并不。
她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会,无论是解谜推理还是热点分析,我总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我实际上只不过是个阿宅。
后来的某一天,我的学妹在写毕业论文时问我,在网络上使用社交媒体ID和现实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还记得自己的回答:“晚华(我的ID)是比我好得多的人,她温柔、聪慧、有同情心、会为弱势群体发声、读过不少书,喜欢的东西也很多。”
“我不是她,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她。或许你听说过拟剧论……算了那不重要,总之,晚华是我的一个可扮演角色,和RPG游戏差不多。”

回到正题,在上海的那一夜里,我和我的网友手牵着手在电影院看了一场外国电影,里面有森林、猴子、原始部落和许多经典好莱坞电影该有的桥段。它绝不是不好看,但也肯定没有好看到我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回忆起主要情节的地步。
电影散场后,我们一起去了地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保持着自己多年来送女孩子一程的良好习惯。她站在地铁口,微微笑着冲我摆了摆手,然后转过身准备回家去。
我叫住了她,走过去给了她一个浅浅的拥抱,在最后分开时,踮起脚尖摸了摸她的头。
“以后也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
在这之后,我考好雅思、出国、和导师与同学斗智斗勇,我和网友彼此不再互通音讯,转眼已是好多年。这一夜的故事被我藏了许久,在某一天的聚会上拿出来和朋友们说时,被嘲笑是在演偶像剧里生离死别的男女主角。
或许你们就要(或者已经)发出疑问,这个故事和游戏有什么关系?
它的结尾是这样的。在我回国并且决定跑去游戏媒体工作以后,我重新登录了久已废弃不用的小号。
和我分别之前,她几乎是个和游戏绝缘的人。但现在她玩起了一款热门的和风养成游戏,抽到了几个SSR,说了不少和游戏有关的话。
我试探性地发出了邀请:“要来我家里玩么?我有很多新买的游戏,Steam库里有好几百个存货呢,你要来试试吗?”
“还是不了吧,有时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