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好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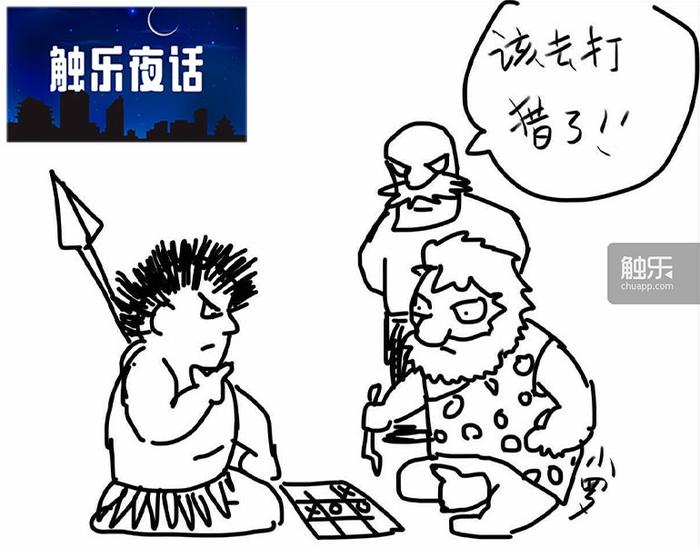
我在国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游戏上,起先,我只想将渐渐积灰的游戏速通,万没想到心理作祟,我又入了《尘埃4》、《马里奥疯兔》、《仁王》以及PS4会员限免的《合金装备5》,光是打通《仁王》第一关的老怪,就用去了我两天时间,我不禁在想,我是在消遣游戏,还是游戏在消遣我,我在玩这一个艰难游戏的时候,是否能达到放松。

关于这点,由于最近抢了朋友的kindle,发现了一本2012年出版的《游戏改变世界》,作者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
在此前,有一种名为“经验取样”的心理学研究,研究方式是抽取不同的人、同一时间点的真实感受,抽取信息分为两类:在做什么以及感觉如何。得出的最常见结果非常违和,那些被我们称为“放松”的事情,比如看电视、发呆、散步,都不会让人感觉好起来,反而会造成轻度抑郁。原因是当我们有了“找点乐子”的想法时,往往是因为我们处于负面压力和焦虑的时候,于是我们主动去找放松的娱乐,设法扭转这些负面情绪。然而,太轻松的乐趣容易把我们推向完全相反的方面,从压力和焦虑变成了无聊和抑郁。
这时更需要的是正面、良性的压力,也就是“艰苦”的娱乐,去刺激肾上腺素、带动注意力与控制力。就像心理学家布莱恩·萨顿史密斯(Brian SuttonSmith)所言:“玩的对立面不是工作,而是抑郁。”
简·麦戈尼格尔认为,主动的游戏使我们集中精力,换句话说,游戏正在跟抑郁对立。当我在紧张投入到《仁王》的游戏时,恰恰产生了各类的积极情绪和体验,激活了我的注意力、激励中心以及情绪和记忆中心。《仁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和室友以简单粗暴的“死一次换人”的方式进行轮换,后来发现,频繁的起身换人这个动作才是整个过程中最累的操作,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死两次再换。
但不得不说,当时我的情绪是满足的,尤其是干掉老怪后,这种满足感达到了顶峰。就从性质上说,《仁王》看起来和现实中的工作雷同,区别在于,现实工作中,我们很难看到自己努力的直接影响,而且相对被动,大部分人从事的艰苦工作,多是因为谋生、出人头地、满足他人期许而“不得不”做的工作,这大大的消减了满足感,更糟糕的情况是,部分人现实生活中的工作“不够艰苦”,当无聊、不被重视等因素围绕在工作里,感觉就像不得不去玩一款垃圾游戏,一周5天,周而复始。
“所有好的游戏都是艰苦的工作,它是我们主动选择且乐在其中的工作。”简·麦戈尼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意识到可以主动激活一个人的身心,甚至为他提供量身定制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生动实时的报告,告诉他完成的进度,清晰的展示他的行为对周围的影响,对,就像游戏一样,使得人们能更为有效的找到合适的“艰苦工作”。
我们追述世界上最古老的游戏,是古代记数游戏《宝石棋》(Mancala,也称非洲棋),然而并没有人记录游戏的起源,唯一可考的游戏记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Histories),希罗多德记载,大约3000年前,阿提斯(Atys)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为王,有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饥荒,起初,人们只是接受命运,翘首期盼丰年尽快到来,然而几年下来,饥荒并没有好转,于是吕底亚人发明了一种“奇怪”的补救方式,他们用一整天的时间来玩游戏,抵消对食物的需求,第二天克制玩游戏进食。依靠这一做法,他们撑过了18年的饥荒,期间发明了骰子、抓子儿(抛抓石子以赌胜负)、球等游戏。

从最早的记载可以看出,游戏的诞生并不是单纯的消遣,而是有目的的“脱逃”现实,游戏利用他的力量填饱“饥渴”,这是游戏其中的一股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如果熟知简·麦戈尼格尔的人会记得他曾于2008年、2009年两次参加了游戏开发者大会(GDC),游戏开发者大会有一个固定的“抱怨”环节,意在为整个行业拉响警钟。简·麦戈尼格尔在2008年受邀在此环节演讲,他说道:“现实已经破碎,而我们需要创造游戏来修复它。”
“修复”这个词颇有深意,这仿佛是逃避现实、镇压游戏外的第三条路,也就是打破游戏和现实间的临界点,跳出原有的尺度,利用游戏设计上所知的一切去弥补现实。
这点得到了游戏行业的共鸣,大会上游戏开发的佼佼者们渴望改变人们对游戏的偏见,其实我们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人们往往对游戏鼓励行事或者塑造人格的论点显得格外警惕。这种偏见根植在文化里,而实质上人们真正警惕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结束、现实开始间的空隙。
哲学家伯纳德·苏茨(Bernard Sutz)做过相关的解释,他提到游戏让我们在无事可做时有事儿做,所以我们才把游戏当做“消遣”,视为填补生活空隙的调剂,但它们远比这些重要得多。
归根结底,游戏的未来需要依靠那些懂得驾驭游戏的力量和潜能、改变现实的人去创造,就像简·麦戈尼格尔这样的人,或许会如他在2009年在GDC上所言,未来25年内,我们能在诺贝尔和平奖前,看到游戏开发者的身影。敬好游戏。
本文论据取自《游戏改变世界》,作者简·麦戈尼格尔,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