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然在想,那些创造了“铸铁块和蓝色的山”以及“以金换金”的译者和编辑平时是干什么的,如果他们能稍微留意一下这些蠢问题,然后把它们纠正了,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吧。

前阵子休假回家,闲来无事读到一篇署名为张治的书评,题为《博尔赫斯研究翻译之名文的汉译指谬》。博尔赫斯是上个世纪阿根廷有名的诗人、作家和翻译家,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博尔赫斯全集》的中译本,而《汉译指谬》这篇书评的作者读到其中《永恒史》一册时,实在读不下去了,他在书评里写道:
须知如此指名道姓评价他人的劳动成果,怎么着手里也得有十足的把柄才好理直气壮吧?继续看下去才发现,这把柄不仅足够理直气壮,而且读来令人哭笑不得:
即使做了多年编辑,隔三差五就见到各种游戏文章里的神翻译,我的第一反应还是震惊于一个资深译者对“Goa”和“the Gold Coast”这样的词条茫然无知,不仅如此,他既不求诸词典,也不检索网络,“以金换金”这样开脑洞式的硬翻译真是比机翻还不如。
但如果说作为译者的刘先生完全对译文不负责任,那也真是冤枉了他。书评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看得出来,这位译者还是稍微抬手查了查“Samun”的来历,只是限于他的知识和能力,不足以弄明白这个词儿到底是不是拼写有误,只好连猜带蒙,强作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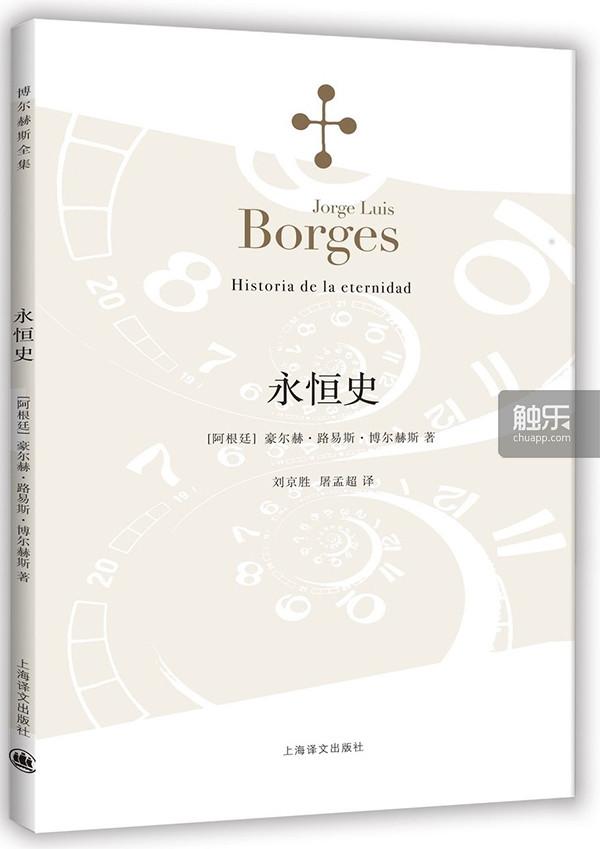
这大概是如今译文界的一个现状。随着最近20年来大量外文作品被翻译进入国内,经典名著也不断出现新的译本,量大了以后泥沙俱下,译文的质量也变得良莠不齐。必须承认,任何时代都出精品,也都有糟粕,但今天的现状是,有很大一部分译文其实都是不够好的。早年间,读着那些著名翻译家翻译的世界名著长大,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这些译本是世界上最棒的,转译而来的中文甚至比原版的字句更加隽永优美。进入新世纪,自从译林出版社出了那部被狂吐槽的《魔戒》之后,我才知道翻译的这潭水有多深。
出版界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心知肚明,而且表现出十分无奈的样子。大多人会解释说,译一本书,经常时间紧、任务急,稿酬还不高,有能力的译者不愿接,接了的人往往还层层转包,包给大学生去开工,再收回来稍加润色即可交稿,所以那些一本有好几个译者的书,书里面人和地名的翻译前后不统一都是常有的事——只要出版社没有认真把关,书也就这样闭着眼出了。往好处想,这种情况下,只要参与了翻译的人还在最后留了个名——你们知道,有些译者本身是学术界或大学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接下了活儿扔给手下带的学生去干,甚至不用给他们署名和支付稿酬。在这样的风气下,你觉得这些堂而皇之翻译出来的“高大上”文学作品比一个草台班子汉化组的质量能好多少呢?
书评读到一半,我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猛地想起家里有本很旧的《堂吉诃德》,以前断断续续看了点,因为读起来啰里啰嗦的(原著大概就是这个调调)一直没有看完,拿出来一瞧,果不其然正是书评里点名的这位刘姓先生所译。这本《堂吉诃德》当年读起来文辞流畅,有什么翻译错误,只要能自圆其说,不对照译文还真是看不出来。所以,这就是出版界多年以来既可以不负责任,步子还能越迈越大的关键,因为普通读者面对低级错漏,要么无法察觉,要么不求甚解,要么根本不会在乎——说真的,傻译傻读才是正常状态。

所以说白了,那些“不幸”被“裱”到网上引起群嘲的译本,说到底还属于少数。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出现,资料的获取没有那么方便和快捷,类似译林版《魔戒》的那些问题也可能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但既然有了网络,有了更多获取知识的渠道,就有人开始重新审视过往那些经典译本,并且开始指出这些译本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时候我读过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感觉很好,如今也被指出有错译的地方,甚至被指责长句太多,英式语法,影响阅读。

至于书评开头提到的董燕生和杨绛先生(钱锺书先生的夫人)的公案,我之前也略有耳闻。董先生是西班牙语教授出身,所以比较有权威,在他看来,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时在词汇含义、句子结构、背景知识的理解上都有错误,而且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20万字,所以他推测肯定有了删节。董先生还说,杨绛把“法老”译成“法拉欧内”,把“亚述”译成“阿西利亚”,是过于自信和缺乏常识的结果,因此杨绛译本在课堂上被他当成“反面教材”,以避免学生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网络上也有人贴出对比文本,指出有些杨绛译对了的地方,反而董先生理解有误。
很多人拿这几个例子替如今翻译界的乱象鸣不平,认为就算有人乱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你看多么有名的前贤也都那么回事。这种看法逻辑上十分奇怪,难道前贤们乱翻了,现代人也乱翻就是对的了?而且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前贤和21世纪的译者们,他们的翻译理念、获取知识的难度和工作环境的差异可谓巨大。
近代以来,可以说开了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之先河的著名翻译家林纾是完全不懂外文的,他的所有翻译作品都依靠懂外文的朋友向他转述大意,消化之后以文言文写成定稿(他也译过一部《堂吉诃德》,名曰《魔侠传》),这种“编译”式的写作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不够严谨的,所以后世的人对他颇有争议,但放在当年的时空条件下去考虑,哪有这么多条条框框。我以前读过一部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亚森罗宾探案集》,至今不知译者是谁,他也是以这种“编译”体选译了几个“亚森罗宾”系列的重要作品,文本明显是清末民初那种半文半白的风格,且明显有一些二次创作式的自我发挥,读起来倒也别有味道。而杨绛的翻译之路更为艰辛曲折,从很多介绍文字里可以得知,为了翻译《堂吉诃德》她自学了西班牙语,后来翻译中赶上了十年浩劫,已经译好的文稿不幸丢失……
这些前辈的译者们可能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也有无心之失,但他们应该没有应付了事、不求甚解和不负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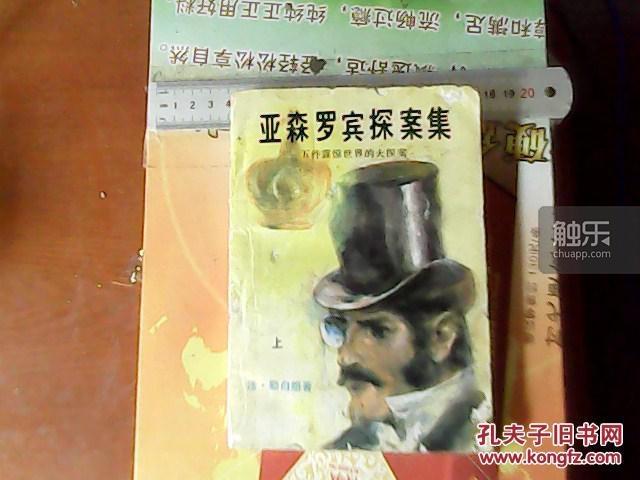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黑翻译界,我的本意是拿这些例子来自省的。
在我家的书架上,就比刘先生译《堂吉诃德》再高一格,摆着一大片的陈年游戏杂志。里面有《大众软件》《大众游戏》《家用电脑与游戏(机)》等当年的一线刊物,也有很多年轻人压根没听过的,比如《游戏时代》《计算机与生活》,这大多数都是上学时每个月翘首以盼的精神食粮,买回来不仅在同学里传阅,传阅完了自己可能还要一读再读。
我一度认为这些杂志都是完美的,但是慢慢的,当我的游戏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发现它们也有各种问题:前瞻胡编乱造的、评论写错了游戏名字和类型的,最令人发指的是,有次一家杂志登了篇超长的《古墓丽影3》攻略,不用照着它攻关游戏,只要读上几段你就会发现,这篇长文完全是以一篇英文攻略为底本翻译而来的,而且翻译者显然没有玩过游戏,以至于绝大部分文句不仅充满机翻语感,而且基本上不知所云。我至今不明白这家杂志登出这篇攻略的心态,抢时效真的高于一切吗?

你看,做一个游戏编辑也时常会面临和翻译界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不管是以前做平媒还是现在做网媒,常常你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向一个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但能写对基本事实的作者约稿,还是向一个文字表达流畅但可能对游戏理解不深的作者约稿呢?尤其是当你知道后者具有“不玩游戏就能脑补出评论而且如同亲自玩过”的能力时?答案不言自明,我必须说,一个文字功底很好但是却喜欢胡说八道的人,给这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可能要比那些看上去能力不足的人要大得多。
所以,我宁愿选前者。编辑工作的基础是什么?是选题能力,是写作能力,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也不能缺了态度——让自己写下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准确、有出处的,而不是依靠你的记忆力、你的理解,或是想当然——人类的记性一般来说都不怎么好,所以必须依靠责任心去保证细节的精确度。
前几天触乐发了一篇译稿,也就是这篇《开发了〈万众狂欢〉的“中文房间”工作室怎么就暂时关门了?》。在最初把原文交给译者之前,我读了文章的前面一部分,文中提到英美文化差异的时候,The Chinese Room的开发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们没有意识到Stile是干什么的。”
何止美国人,可能全世界的人也不知道“Stile”是干什么的。我和译者交流了一下,“Stile”这个词在词典里有多种意思,但似乎都跟游戏里的情境对不上。琢磨了半天,直到搜到一张“Stile”的图片,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游戏里一个独特的梯子状出口,如果没有图片提示,我俩已经把这个游戏里的设定给忘了(毕竟通关一年多了),如果碰上一个没有玩过这游戏的译者或是编辑,天知道他最后能连猜带蒙翻成什么……
后来我特意去把游戏下载回来,重新进去截了一张“Stile”的图片作为译文的配图,我想这对读者来说应该比文字的解释更直观。

至今我仍然在想,那些创造了“铸铁块和蓝色的山”以及“以金换金”的译者和编辑平时是干什么的,如果他们能稍微留意一下这些蠢问题,然后把它们纠正了,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