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少有人把玩游戏的老年人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玩家。他们在游戏里的生活、他们对游戏投入的感情、他们在游戏中收获的意义,长久以来都是被忽视的。就像在家庭中的角色一样,老人们不太为自己出声——但他们是重要的存在。
老年人在游戏玩家中是一个几乎隐形的群体。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几个玩游戏的老人。可能是那个痴迷于在线象棋、抱着手机不撒手的爷爷,也可能是那个为了领取体力、每天凌晨都会分享游戏截图到朋友圈的外婆。但很少有人把这些老年人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玩家。
有些人也许会关心老年人的游戏时间是不是太长,也有些人可能会关心他们每天是不是睡得太晚,但很少有人问过他们对游戏投入了怎样的感情,在游戏中得到了什么,又如何看待游戏的意义。
长久以来,针对老年群体的玩家画像是缺失的。在屏幕的另一端实力突围的可能是一位打到了“荣耀皇冠”的退休阿姨;在《我的世界》里被小男孩表白的可能是一个年过60的“小姐姐”。一些在我们看来已然是老古董的游戏,对他们来说依然新鲜有趣:在《黑道圣徒2》里打了2500小时的大爷究竟在想些什么?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些玩游戏的老人们是不是比其他老人走得更前?
通常情况下,老人们都是沉默的。又或者,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想说什么。
退休之后,邢大爷明显感觉到自己关注新事物的心力大不如前了。
邢大爷在铁路上工作了40年,刚退下来的那两年,他天天出门找人打麻将,偶尔去别的城市旅个游。他隐约知道外面的世界发展越来越快,但他不关心这些。
“他们老跟我说,把网络这个东西弄弄好,什么都方便。购物方便,看东西方便,知道的东西也多。”邢大爷说,“我说,我干了那么多年铁路什么不知道?”
外甥周林一个劲地怂恿他,学学这个,玩玩那个,还直接把自己Steam帐号分享给他,先筛出他的电脑配置跑得动的,再从中挑选出他可能会喜欢的游戏,让他挨个尝试一遍。
结果,邢大爷被《黑道圣徒2》击中了。从2017年12月份至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黑道圣徒2》里花了250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花上将近4个小时。“有时候玩一天,有时候玩着玩着就玩到半夜,有时候上去了就下不来。”邢大爷告诉我。

他被这个游戏深深地迷住了。“这里头设计的人物好像都有思想,我做什么动作,他回一个动作,我感觉老么奇怪了,弄得挺神秘似的。”他觉得这个游戏中可钻研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仅仅通关还不够,他对里面的小游戏也非常好奇,老想着“把这东西彻底玩完,看看里头的内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像着了魔一样,一天到晚,邢大爷心里头就老琢磨这个游戏。“心头老挂着这个事,出门办事也只想着赶快回家玩。”
邢大爷对《黑道圣徒2》的执着令外甥周林感到迷惑又无奈。他试图给邢大爷推荐其他的游戏,但邢大爷就是不肯换。
周林给了我一张清单,上面记录了邢大爷尝试的每一款游戏,以及邢大爷不喜欢它们的原因。“《Portal 2》,不感兴趣;《足球经理2018》,不想当官;《ICEY》,难操作,字太小;《这就是警察》,节奏太慢;《热血无赖》,难操作,只看景,能回忆香港旅游;Xbox 360体感游戏,不想活动……”

清单上有20几款游戏,但在邢大爷眼中,这些都不如《黑道圣徒2》“来劲儿”。就算是“黑道圣徒”系列,他也独独钟情于2。周林给他装上了更新的3和4代,尝试以失败告终,“他说3和4剧情太扯淡”,周林对我说。
提起自己对于《黑道圣徒2》的着迷,邢大爷颇为自得。“周林昨天还来我这儿,又说让我换个游戏玩,我说不换,肯定不换,有生之年不可能换了,别的游戏都换了也不能把它换了。”
邢大爷也知道《黑道圣徒2》是个老游戏,“我听他们说,这个游戏是09年的,早已经过时了。”但这并不能改变邢大爷对这款游戏的执着,“我也不知道它的设计者后面给留的什么悬念,我就对这个挺感兴趣。”
“怎么?你们对这个事不感兴趣吗?”邢大爷问我。
刘阿姨玩的游戏同样也非常古老:《祖玛》《空当接龙》《植物大战僵尸》……这些游戏她轮换着玩,每天要玩上六七个小时。
刘阿姨起初不怎么玩游戏,但当女儿去了北京工作之后,只剩下丈夫、婆婆和她3个老人在家,她感觉家里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我可不得搞得热闹些吗?”为了哄老太太开心,刘阿姨玩起了一些小游戏,有时候老太太在一旁看着,有时候也和她一块玩。
“原来我跟她奶奶下跳棋、打扑克,后来她奶奶眼睛不好了,只能看得见球了,所以我就陪她打《祖玛》,老人家高兴。”
“高兴”二字始终贯穿着刘阿姨对于游戏的感受。一开始,她玩游戏是为了让上一代高兴;老太太几年前去世后,她自己一个人玩,越玩越喜欢,心里头也高兴。每天把家里的事情做完,其他时间都在电脑前打游戏。
对刘阿姨来说,玩游戏也是在学习新鲜事物——虽然她玩的那些游戏已经不再新鲜了,但她依然觉得有意思。她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是《植物大战僵尸》,“说实在的,我给制作游戏的人叫好,你知道吧,这个人他弄的小僵尸也太好玩了,不跟你吵架,不给你发脾气,你喜欢玩哪个就玩哪个,锤僵尸锤得我可高兴了。”

她时不时会让闺女给她下载新游戏,自己一个一个琢磨着玩。“比方说《愤怒的小鸟》《水晶连连看》什么的,反正我要学的好多,不会的我都学。”现在手头上的几个游戏,刘阿姨天天都打,除了觉得游戏好玩以外,“我也怕我忘掉怎么打”。
刘阿姨住石家庄,离北京不远,但跟女儿还是不常见面。“见她一面不容易,见了她以后我光想学点东西。”刘阿姨总盼着女儿多回来几趟,“我要跟她在一起,我老早学会好多东西了。我不知道她脑袋瓜里到底有多少东西,反正我见了她就得赶紧学。”
以前刘阿姨还有更丰富的娱乐活动,比如中老年迪斯科,她跳了整整17年。但后来搬了家,从桥西搬到桥东,舞友们都留在了另一头。还有一回,她在户外玩得太过头,又是跳舞,又是打羽毛球,又是打篮球,“这么一搞,后来腿就出了毛病”。
有了游戏以后,刘阿姨就算在家待着也总有事可做。“这个小游戏不是一般地好玩哦!”刘阿姨拔高语调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坐在这儿就想先打它们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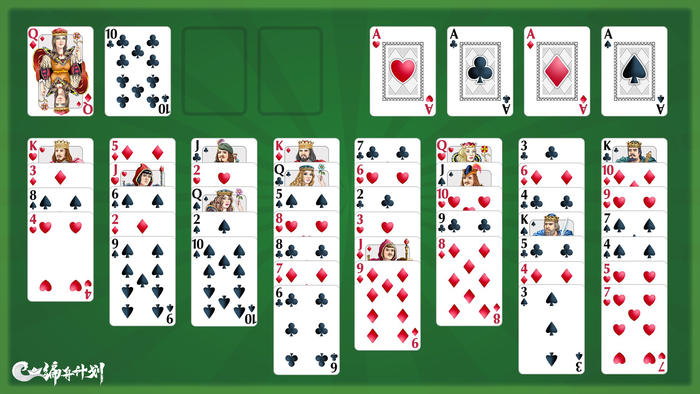
刘阿姨不觉得游戏分什么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或者分什么新和旧,“各人有各人的脾性,谁跟谁喜欢的也不一样,管不着别人。”刘阿姨说,“我们成天不就是为了身边的人活着、也为自己活着吗?大家玩着,高兴就行。”
朱阿姨后来才明白,《我的世界》这个游戏,“玩家们的年纪都蛮小的”。这些小朋友们有自己的规矩:在这个低龄玩家占绝对多数的游戏圈里,像她这种年龄的老人家是不太受欢迎的。
之所以会被人识破,是因为她一开始的游戏ID叫作“爱妞宝的婆婆”——她有一个叫作妞妞的外孙女。玩了一段时间,她加入了几个游戏QQ群。群里的小孩子们看到这个名字,问她“你是嬷嬷吗”,她没什么心眼,回答“是呀是呀”,立马就被踢了出去。
为了能够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朱阿姨赶紧把她在游戏中的名字改成了“宝莉小马”,因为她喜欢看那个动画片。她还向外孙女妞妞请教,妞妞给她支招:“婆婆,以后再有人问你年龄,你就不要说话。”
朱阿姨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玩《我的世界》,这个游戏是儿子给她推荐的。“那个时候我没有事做,心里面蛮寂寞的,觉得很空。”朱阿姨说,“儿子就给我下载了这个‘MC’,说老妈你可以在里头种种田、养养猫什么的。”

自从有了这个游戏,朱阿姨几乎每天都玩——在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游戏里生气:房间里的床昨天好像被人睡过了,她被莫名其妙地传送到了主城。为了接受我的采访,朱阿姨表示可以暂时挂机一下。虽然在挂机的状态,朱阿姨还是放心不下,时不时地回去看一眼。
“姑娘你等一下哦,有怪来了。”朱阿姨说,“我正挂机呢,他们把我送到旷野上了……等等怪要来把我打死掉了,我上去跟他们说一下哦。”
这样反复了几次,朱阿姨一会儿查看一下自己的状态,一会儿给游戏中的其他玩家留言,委托他们解决自己“床被人睡过了,回不去了”的问题。在电话那头,我听到朱阿姨耐心地给捣乱的小朋友发语音:“你怎么睡我的床呢?我都写到牌子上了,‘宝莉的床,谢谢,别睡我的床’,你还睡!虽然你昨天给了我两个村民,我非常感激你,但是你把我赶出来了,我怎么办,对吧?”

朱阿姨的声音很年轻,只听声音的话,说是二三十岁也不会惹人怀疑。换了新名字后,朱阿姨算是在游戏中站稳了脚跟。她在游戏里的好友列表越来越长,加的QQ群也越来越多。
小朋友们只当她是年纪稍大的“姐姐”,一到下午,朱阿姨的QQ就热闹了起来,很多小朋友来敲她:“姐姐你不玩游戏吗?玩不玩呀,玩不玩?”朱阿姨总是禁不住这样的呼唤。“看他们那么热情,我就上游戏跟他们一块玩了。”
“姐姐”甚至遇到过要跟她“交朋友”的男孩。
“有时候碰到那些不太懂事的男孩子,说姐姐我们交朋友吧,我说我们不是已经是游戏好友了吗?他说我们交另外一种朋友。”朱阿姨笑着说,“我说不行,我多大呀,你都没见过我,怎么交朋友?他说,交朋友不就可以见面了吗?”
朱阿姨心一软,差点就要跟他讲出实情。“我想跟他说,我还有自己‘灰暗’的一面呢!”但想了想,她还是作罢了,“一说他们把我踢出去的话,我就没得玩啦!”
游戏里的朋友们对朱阿姨而言特别重要。刚开始玩《我的世界》时,朱阿姨特别害怕怪物,“看到怪我就跑呀,我也没有好的武器,都是自己砍树,做一些木头的工具之类的,又没有盔甲什么的,很惨的。”一个人开创造模式玩,朱阿姨也觉得有点无聊,“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看到怪我又不敢下来”。
跟朋友们玩在一块后,朱阿姨在游戏中体会到了幸福感。“他们帮了我很多。有时候看到我,他们知道我怕怪,冲到我前面就把怪打死了。”朱阿姨说,“我最近玩‘空岛’嘛,掌握不好自己的步数,不小心就掉下去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又重生,后来他们那些小男孩也会帮我把路开得宽宽的,然后跟我讲,小姐姐你不要往边上走。”
“他们真的蛮关心我的,有一种暖心……那种暖心的感觉。”朱阿姨说,“玩了‘MC’之后,我没那么寂寞了。”
就像被踢出群的朱阿姨一样,游戏的世界对待老年人可能并不友好。老年玩家在游戏中常常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年龄歧视。
尤其是在玩线上多人联机的游戏时,老人们往往会很快地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年龄在游戏的世界里是个敏感词——而这种歧视几乎就是冲着年龄来的,往往与实际的游戏水平无关。
在《和平精英》中最好战绩打到过“荣耀皇冠”级别的李阿姨也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年龄。“有时候他们听我说话的口气,会觉得我有点年纪。” 遇到这种可能会“暴露年龄”的情况时,她一般就含混过去,“我就告诉他们,是啊,我是你姐,不是你妹呀……我是真的不敢告诉他们年龄,我怕他们知道了以后,就不和我玩了。”

刚开始玩的时候,李阿姨老是不敢跟别人打,打四人排位时她总揣着担心,“变成人家的累赘不太好”,所以等儿子有空的时候,就让他带自己一把。儿子也有一群朋友一起玩,就把她拖到那个群里去玩了几天。
“他们一帮年轻人都特惊奇,问我:‘阿姨你也会打吗!’”李阿姨说,“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但听他们的口气就知道他们很惊讶——好像在说:怎么这么大岁数的人还在玩这个游戏!”
李阿姨连忙对他们说:“我很菜的,我跟你们混,跟在你们后面就行了。”
没玩几次,李阿姨就发现,这帮年轻人工作都忙,人总是凑不齐,不能经常陪她玩。打了几天,李阿姨觉得在他们那里学不到东西了,提高不了打游戏的水平,就去找直播看,跟着主播们学。
“刚开始真的很菜,有人过来,我听到声音连东南西北都搞不灵清的。”在主播们的“指导”下,李阿姨的游戏水平迅猛提升。“直播里面它会教你很多东西!你去看这些主播们打——虽然他们都是很刚的,但也会教很多很多东西,战术、战略都得到了提升。”

在普遍倾向于休闲游戏的中老年女性玩家中,李阿姨对《和平精英》的爱好显得有些特别。李阿姨对打枪的喜好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上世纪90年代初,20多岁的李阿姨在中国电信做话务员,参加过通讯兵的预备役。“我那个时候喜欢上打枪了。我们有打实弹的实战演习,我都打得挺好的,所以看到玩枪的游戏我就很感兴趣。”
如今,她在游戏里有了一些固定的战友。他们的年纪有大有小,但就像李阿姨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实际年龄一样,李阿姨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只能猜个大概。李阿姨很满意目前的状态,“太遥远的东西也没必要搞清楚,玩玩可以,他们要加微信我都不加的”。跟线上的朋友们相处的时候,她始终维持着一定的模糊地带。
李阿姨早已不跟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一块玩了。“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嘛。” 她被同乡的朋友拉到一个叫作“Welcometo 浙战”的兵团里,里头都是浙江人,除了日常稳定的搭档以外,李阿姨有时也会和兵团里的人一起玩。
“我老公经常说我一打游戏就叽里呱啦,因为我戴着耳机自己说话声音有多响也不知道,就跟着里头的人一直嘻嘻哈哈,他老说我吵的。”李阿姨笑着说。
一方面,老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越来越多地接触游戏了;另一方面,那些原本就玩游戏的人也变老了。
90年代,雨哥就已经买了红白机,玩上了当时流行的《魂斗罗》和《超级玛丽》,“这个可能是最早的游戏机了,不知道你们这代玩过没有”。后来他又置办了电脑,“有了电脑就开始玩‘生化’,玩‘极品飞车’……对了,‘CS’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玩的。”雨哥说,“电脑就是玩游戏最好,最考验电脑硬件的不都是游戏么?”

雨哥以前是工程师,2000年出头那会儿,经常跑到各个地方修高速公路。有一回住到了山里,他就跟手下干活的小伙子们弄了几台电脑,连上网线一起打CS。“那时候没有无线网,我们就连个局域网,没事干就玩呀,住山沟里头,离城里50多公里,也只能玩这个。”雨哥说,“一打发现我级别比他们还高,这些小伙子晚上没事儿就拉着我玩,好家伙,完了非请我吃烧烤。”
后来他买了PS3,“那会儿我跑外地工作的时候,来回坐火车坐飞机我都一直带着那玩意儿。”到了单位,他就把游戏机接上电视玩。
作为一名老强者,雨哥一直都走在时代的前沿,游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从长城386时代就已经接触了电脑,在单位里学制图、学办公软件、学五笔输入法,他都比人更快;至今用的电脑也是用儿子“淘汰下来的破玩意儿”,自己买零件拆装,熟练得很,“全都自个儿弄”。
他在《穿越火线》里打了足足11年,去年练到了满级——五星大元帅。因为打得好,他去年被招进了一支战队。跟游戏里“那些名字花里胡哨”的战队不同,雨哥的这一支战队名字朴素得多,叫作“老年夕阳红”。瞧这名字,“我估摸着里头的人可能岁数都不小”,雨哥说。

加入归加入,雨哥在战队里挂了个名儿,但几乎从不参加战队的活动。“他们还要训练什么的,我可没时间。”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尤其是满级以后,虽然还能接着往上升,“上面还有个紫金大元首呢”,但已经打到这份上,他也不太着急了,每天上游戏就感到很威风。
“我这打人家那简直——我跟你说,那不一样的!我以前就是受虐,现在虐别人,那能一样吗?”雨哥说。
退休之后,雨哥基本上都在专攻《穿越火线》,每天会玩上五六小时,但每隔一两个小时他就会休息一会儿。“每一把大概半个小时,打三四把我就不打了。”雨哥说,“打到那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脖子也硬了,老是朝着一个方向,一转头那个骨头就咯咯响。而且按着鼠标的时候小指头一直是伸直的,打的时间长了手指头弯都弯不过来,还得用手掰它一下子……不得劲儿嘛。”
在休息的时候,雨哥也闲不下来。“我还得磨戒指、画素描、弹吉他呢,玩相机我也挺内行的。”雨哥说,“我还有好多其他事儿,以前还爬山徒步,北京的山我都爬遍了。”
对雨哥来说,游戏只是他退休生活的娱乐项目之一。“游戏嘛,你适当控制它的节奏,就是个健康爱好。”因为有着这样的生活态度,雨哥认为自己至今也还算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什么淘宝网购、移动支付,雨哥都是最早的那一批用户,“这些东西能有多难哪?你老觉得这些东西挺难不去接触,这个也难那个也难,最后啥也干不了了。”
“社会在进步,你不能当一个啥都不知道的人。”雨哥说,“咱得跟上时代是吧,不能让时代给咱落了。”
他不担心自己有一天会玩不了游戏,回答得十分爽快:“人生这个路,大家伙都差不了多少,玩不了就玩不了了,也没什么遗憾了。这么个岁数,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
至少在当下,雨哥说,“你得兴奋起来”。
对于老年人玩游戏,一直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游戏对老年人有用。相关的讨论在《Pokémon Go》风靡中老年人群时曾经达到一个顶峰,痴迷于抓小精灵的老人们为了游戏走出家门,既锻炼了身体,又找到了与当下的社会接轨的方式。
如今,与老年人相关的游戏研究越来越多,大部分都聚焦于游戏的功能属性上。有的游戏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反应速度和认知能力;有的游戏能够促进海马体灰质的产生,对缓解老年痴呆症有作用。因此,游戏常常被当作一种治疗的手段。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的成果的确为游戏洗脱了一些“原罪”,但也形成了一种惯性:仿佛谈到老年人和游戏,“功能”和“效用”就是唯一的打开方式。
当然,只要保持在一定的游玩程度,游戏对于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是有帮助的。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老人们往往会立刻告诉我,游戏对他们颇有益处。
“最起码……最起码手没那么笨,脑袋也没那么笨吧。”雨哥对我说,“这个手指啊,你来回操作,上蹿下跳、开枪瞄准,都需要一定灵活度。”
“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在家里玩了游戏,其他的一些事儿就玩不了了。”雨哥笑着说,“像抽烟、喝酒、赌博,可不就避免了吗?”
对于这些老年人们来说,游戏的效用使得游戏成为退休生活的娱乐选项之一,但他们会一天一天地玩进去,还是因为游戏本身给他们带来的乐趣。
“开心!玩了游戏就非常开心。”朱阿姨告诉我,在自己玩游戏之前,她讨厌儿子玩游戏,只是从原则上理解“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只要不影响功课,她就不干涉。在自己玩游戏之后,她才明白了游戏的魅力。
朱阿姨让我加她的游戏QQ号,进她的空间看看。她的状态和相册里除了外孙女的照片以外,几乎都是《我的世界》有关的图片,有的是玩家在游戏里建造的怪建筑,也有她自己的游戏截图。
“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激动。”朱阿姨说。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老人们对自己的游戏时间还是有所克制的,他们也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调剂。有时候是在做饭,“蒸上包子之后,过几分钟我就得放下游戏去看一眼”,刘阿姨说。有时候是其他的娱乐活动。“我打太极拳、游泳,还在家里养了一大堆花。”李阿姨告诉我,“下午我一般吹葫芦丝,葫芦丝练好了我才去玩游戏——我觉得《和平精英》和练葫芦丝也差不多的,都讲究听力和反应。”
有时候玩得过头,邢大爷偶尔也会感觉到身体健康状态不太理想。眼睛、颈椎、腰,在电脑前坐得久了总会出点毛病,但邢大爷对这些不太在意。“干铁路的时候也是东跑西闯的,这么多年都习惯了,不在乎这些。”邢大爷说,“游戏打久了,有点问题也不要紧,治不就完了。”
老年人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多样化的群体。当我们将目光放在这些老人身上,试图了解他们在玩什么、想什么,并且为他们发出一点声音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些老人的背后是一个更广阔、更多元、更难以触及的社会图景。事实上,能够被我们看到的这些老人几乎是老人中状况最良好的一批:他们多半曾经从事着一份体面的工作,退休后也有着充实的活动安排,与子女关系良好,经济上较为宽裕,生理和精神状态都还算健康。
这显然不是巧合。从某种程度上,不是他们选中了游戏,而是游戏作为一种具有科技属性的现代产品,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老年人才能好好享受到游戏的乐趣——不仅玩,而且是健康地玩。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60岁及以上人口将近2.5亿,其中超过4000万是失能失智老人,这意味着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和基本的认知能力——这一部分的老人只会比其他老人更加沉默。如果他们也玩游戏,那么游戏在他们生活中的地位会不会更加重要?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群体是独居老人。他们或许身体和头脑都还健康,但他们的情感需求却得不到满足。
“如果从情感寄托的角度上讲,这样的老人有没有权利主动选择不跟外界沟通,而是沉迷于一些能够给他提供补偿作用的游戏?当他们失去了过去在工作中那些良性互动、有来有往的社交关系,有没有可能在游戏中寻找作为社会角色的另一种存在感?”老龄社会30人论坛秘书长唐颖认为,对于老年人玩游戏的现象的探讨应该有更多的维度,对于老年人群体也应该有更多人文角度的关怀。

唐颖认为,当我们讨论老年人玩游戏时,更合理的划分不是按照年龄,而是按照生存状态。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并不会一过60岁就变成失去生活能力的傻瓜。许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仍然处在活力充沛的健康老龄期,正要开启自己的“第三人生”。
“对生存状态好的老人来说,他们玩游戏的需求,我认为跟其他所有玩游戏的人的需求是一样的。”唐颖说。但事实上,许多老人玩游戏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不被身边人理解,而他们在游戏里也要隐瞒自己的年龄,以获得其他年轻玩家的接纳。像朱阿姨一样成功地和小朋友玩成一片的老年人自然很“酷”,但为什么只有够“酷”、懂得如何融入年轻人的老人们才有资格享受到游戏的乐趣呢?
“老年人在游戏中遭遇的年龄歧视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公共问题。”唐颖告诉我,“我们如何去对待年长的人?我们如何理解年长的人的一些社会行为给我们造成的影响?”
随着社会逐步走向老龄化,这样的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全国老龄委2015年发布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我国的老龄人口将会不断增加,到2053年达到峰值4.87亿人,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将一直维持在3.8亿到4亿之间,占人口的三分之一——那正是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间。
唐颖告诉我,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也会变成未来的老人”。此刻正在有着话语权的这一代人,也会走向苍老,走向退休,走到时代的聚光灯之外,变成又一个沉默的边缘群体。
“所谓的前辈们,也只是活在自己的时代里。在合适的时间点,他们也拥有过自己的话语权。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要被自然而然地淘汰掉,被漠视、被歧视,甚至被敌视呢?”唐颖告诉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年长的群体要尽可能地跟上时代的变化,另一个是年轻人要对老年人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因为所有人都会变老。
就像采访中这些老年人一样,曾经他们可能是时代的“弄潮儿”,玩的都是最新的游戏机,赶在所有人前头;如今他们可能连学习那些不再时髦的游戏都感到费劲,不敢在其他玩家面前暴露自己的年纪,或者更愿意守在一个10多年的老游戏里一天一天地玩下去。
1996、1997年那会儿,邢大爷40多岁,给儿子买了任天堂的游戏机,自己倒玩上瘾了。“那时候不合眼地玩,玩迷了。什么‘俄罗斯方块’、‘超级玛丽’系列,买了很多游戏卡,插卡玩的。”家里买不起两部游戏机,邢大爷跟儿子抢着玩。
他喜欢玩儿,不止玩游戏,也玩其他东西——但由于条件的限制,这成了他在年轻时没能完成的梦。“年轻的时候,我好这个好那个,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哪个不好?也好玩游戏。但那会儿我净忙着上山下乡,要么家里穷没条件,要么根本就没这些东西。”邢大爷说,“说实在的,全耽误了,没赶上好时代。”
到了退休的岁数,条件是有了,但邢大爷感到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渴望也差不多消失了。一开始,他对于现在的科技产品根本提不起兴致,嘴上说着“我干了这么多年铁路什么事情不知道”,事实上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没那个劲头了”。
“对这些事情不熟悉了,不感兴趣了,脑子不好动了,人不好钻研了。”邢大爷对我说,“昨天我还在说,电子产品淘汰太快了,根本就跟不上,要是没有年轻人带着,你进不去。”

在外甥的鼓动下,他开始用手机,玩电脑,但他喜欢打的游戏也就那一个。“对这个游戏,我肯定就千方百计动脑子,我钻进去玩,但对其他东西我就不想动脑了,觉得自己不是年轻人那块料了。”
在邢大爷还年轻的那几年,他工作忙,没时间想别的。每天上班路上,他都会经过大连友好广场那一块。“那一片全是游戏厅,那时候大家都在游戏厅里打游戏,你知道吧,什么赛车,什么僵尸,那画面确实好看。”
游戏厅里的“僵尸”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退休之后他终于有了时间,想起当年路过游戏厅的画面,他就跟外甥说:“有什么打僵尸的游戏也给我安上几个。”
邢大爷已经叫不上来那些游戏的名字了。“也挺好玩的,就……四五个人打僵尸,有点儿恐怖的意思。”邢大爷说,但是打了一段时间后,他慢慢也不感兴趣了。
“那个年代过去了。”他说。
好在他遇到了《黑道圣徒2》。“这一打正好,我就不撒手了。”邢大爷很是满意。在我写完这篇文章,向外甥周林要一张邢大爷的Steam截图时,我发现邢大爷的游戏时长已经超过2600小时。
他是真喜欢。

“你说,他到底在游戏里做什么呢?”我问周林。
“我也不知道……他的话,最感兴趣的可能也就几件事儿。”周林说,“一个是开飞机在天上飞,一个是开大卡车堵高速公路,再有就是蹲在地铁上。”
“蹲在地铁上干嘛?”
“在地铁上……”他想了想,“看看城市吧。”
(本文由今日头条游戏频道“编舟计划”独家支持,今日头条首发。编舟计划, 用文字将游戏与时代编织相结。每周一篇,敬请期待。未经授权,内容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