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在于保持沉默,身心投入。一旦默契被打破,开始用上成年人的语言,它就变成了另一个游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端游玩家见证过一种互联网奇观:在服务器内,通过喊话道具公开刷屏,让所有人都听见你——你对某人的爱情、你对某人的侮辱。在那里,语言是有形状的,每个字都要占据几个像素的空间。如果将聊天列表无限制地展开,我们会看到一些人的话足有纽约帝国大厦一样明显,肥硕臃肿,遮天蔽日。有些人的话语则如雪泥鸿爪,渺不可查。
共同的是,所有的话语都会戛然而止。

传播学上说,“媒介即信息”。一个相对通俗的理解是,传达信息的手段本身就在决定信息的内容。在电子游戏领域,本质上,交流也是游戏的一部分,交流的方式则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在商业思路主导游戏设计的情况下,有些游戏把交流变成一种具有稀缺性的权力,需要金钱购买。付出面额不等的钞票,购买你的音量大小、购买你发声的位置。如果你足够有钱,整个对话框都是你的罗马剧院,使声音回荡、重叠、环绕四方。
这种设计其实是在游戏里玩着现实。本质上,参与的每个玩家都在“出戏”。不过,在设计师主导沟通机制的一些情况下,沟通机制不但不令人出戏,反而还会巧妙地强化玩家对游戏氛围的浸入,使你真正成为“你”。
写这篇小文章,是为了讲述几段在游戏里与沟通有关的体验——出戏的体验、入戏的体验,以及由入而出的体验。
我最美好也是最尴尬的一段出戏的沟通,发生于《最后生还者》的联网模式中。
2019年,我刚刚辞掉上一份工作,在家里休息的时候,觉得时间停滞了。为了安抚折磨人的寂寞感,我擦干PS4的灰尘,放进《最后生还者》的光碟,联上网络。我记得自己当时的ID名称是“SlowWalkingMan”(慢慢走的男人)。
那天,我随机匹配了一场游戏,发现自己扮演一个穿着破烂、胡子拉碴的流浪汉,手上拿着一把突击步枪。身旁还有两个脏兮兮的伙伴,耳机里传来一阵又一阵模糊、遥远的说话声,是美式英语。
日常场景里的英语总是给我一种奇怪的、过分亲密的感觉,尤其是从美国青少年的嘴里说出来。那是一种粘稠的、慵懒的、拖得太长的东西,字与字、词与词抱成一团,难分彼此。
在通话噪音的掩蔽下,我觉得好像有两个没睡好的男高中生,和我一起躺在一顶防水布做的帐篷里,里面十分拥挤,而且随便动一下都会引起布料摩擦的沙沙声。他们俩对你置之不理,交头接耳个不停,就在你的耳旁,热气呼在你脸上。声音听起来又那样私密。我是个害羞的人,开着麦克,不敢说话。
一开始,他们好像在说一件私人的事,清晰地听到了“父亲”“制作”“木头”“梅赛德斯”……但说不清楚他们究竟在讲什么——父亲用木头造出了一辆梅赛德斯?
当我无缘无故死了好几次之后,他们似乎开始抱怨我。以下是我根据记忆翻译的内容,我会把所有的脏字都用“×”表示。
“三连……×我,×死我吧。”一个人说。
“实在太……糟心了,也×死我吧。”另一个人说。
接着,他们开始谈论我这个沉默的队友。伴随着肥胖的感叹词、嬉笑的系动词和冷嘲嘲讽的形容词。“老天……我的意思是,这家伙以为自己在干嘛呢?”
“×!真的,简直无话可说了,是的。”
我感到冒犯,朝他们耳旁开了一枪。
“嘿,他还是会开枪的。好×样的,老伙计。”
“哇哦,简直是……天才,一个天才。”
我屏住呼吸,没有说话,朝着一堆集装箱跑离他们。
“慢慢走的男人……跑……了……起来!”
“哈哈,好样的,慢慢走的男人,飞奔向……死亡!”

我抱着枪,朝一个转角冲去,即将离开他们的视线,可是突然从那里冲出来一个敌人,手里拿着一样近战武器。我不太记得是什么武器了,也许是一把斧头,也许就是步枪的枪托?他冲入我怀里,朝着我的胸口来了几下,直到我跪倒在地。另外两个人一边笑一边围过来,开枪把敌人打死。
我本以为他们不愿带我玩了,奇怪的是,游戏一直在继续。他们乐此不彼地嘲讽我,而我也置若罔闻。我们默契地在羞辱与漠视之间维护着一种平衡。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毫不反抗,不去回应侮辱,他们的拳头就打不到地方,他们又不了解我,来自异国的遥远声音无法真正伤害到我,反而让我觉得受到一种密切的关注。
对于他们来说,这同样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首先,他们水平很高,靠俩人就能和对方打成平手。其次,我也没有刻意捣乱。我水平虽然差,但他们看得出来我在努力——我是“慢慢走的男人”,为了讨取他们的欢欣而蹦跳狂奔。于是,他们嘲讽我的同时,又不无爱怜之意。
“嘿,慢慢走的男人,跟……我来。”
“为什么不……说话呢?慢慢走的男人。”
“他……是个×害羞的慢走之王。”
“他没有成年,在瞒着爸妈打游戏。”
“什……么?你怎么知道。”
“嘿……兄弟,仔细听……”
“什……么?”
“闭嘴听,他开了麦没说话,一直在呼吸。感受一下那轻柔的呼吸,就像……夏日吹拂窗帘的风。”
“(沉默了一会儿)哇……我听到了。”
“感觉怎么样?”
“像个女孩,我××的上帝×啊,一个女孩。”
“嘿,女孩,我真滴很抱歉。”
“现在,我们都别说话了,×,一个小妞,天啊。”
“小妞小妞小妞小……妞!”
其中一个哼起了歌,里面是小妞这、小妞那的,我完全听不懂。我看了看表,这时是星期三下午4点,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点。一个百无聊赖的成年人没有在工作,没有为社会尽他的一份责任,而两个百无聊赖的美国年轻人窝在床上唱歌、大笑、把被子踢得乱七八糟,准备睡过第二天的希腊哲学课。
他们的家长一定很伤心,而我爹随时可能打来电话抱怨。这种状况让我有些难过,但与此同时我又找到了自己寻觅的东西。一种和其他人共存、惺惺相惜的体验。这是我最尴尬、最美好的一次出戏。
我只要一开口,就会破坏这种体验。
有时候,沉默在艺术家手上变成一种有意义的设计,在根本上融入了游戏机制,创造出令人着迷的氛围,使人在与他者沟通时,仍然保持了“入戏”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我印象中做得最好的游戏制作人,是宫崎英高先生。

在我最钟爱的“黑暗之魂”系列里。玩家扮演的角色不能说话、不能打字,只能做一系列的姿势,比如招手、下指、雀跃、鞠躬。
在保留最有效的、符合游戏风格的沟通方式后,“黑暗之魂”过滤掉了破坏游戏氛围的杂音。当我穿着一身银色铠甲,漫步在那些光怪陆离的村庄、颇具史诗意境的宏伟宫殿下时,我不想听到有人跟我说东北话,或者在屏幕中打出任何诙谐的网络用语。宫崎英高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一次有效的扮演,助一群人抽离肉身的经验,进入古雅的洪荒。在里面,每个人的姿态都很优雅,缄默但是值得重视。这样的心态,说是逃避也好——逃避喧哗、聒噪、虚张声势的现实。
在“黑暗之魂”系列里,我最喜欢看别人做的姿势,是太阳骑士降临的姿势。太阳骑士是一种联网用的身份,担任太阳骑士的人可以帮助其他玩家攻克那些艰难的Boss。他们出现在画面中时,身体摆成一个壮烈的V字,在永远的黄昏的烘托下,几乎使人萌生敬意。
金色的身躯散发出光芒,充满着希望。这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肢体动作。在经历了那么多次挫败后,你又重新感到了力量,而任何凡人的言语都会损害它带给你的慰藉。

我自己最经常使用的动作是双膝下跪,朝着在关卡末尾入侵我的PvP玩家连连磕头,祈求他们饶我一条小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路跑来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想再被这些流氓打死,导致前功尽弃。在这方面,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下跪常常是非常有效的,任何一个冲着你杀过来的人,看见你行此大礼,都会产生一点恻隐之心。他们不一定会走,只会朝你无奈地摊开手,或者郑重地鞠一躬,然后接着过来砍你。
没关系,跑远点,继续下跪。他们就知道你有些难处了,可能会犹豫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有时会选择离开。但有时,他们会慢慢走近,却不急着攻击。我会算好时机,突然偷袭。
这种做法并不雅观,但我完全能承受一个下指的手势,也不觉得出戏。毕竟,这些事在游戏具有末日特色的美学框架内是完全成立的——你可以展示骑士的精神,也可以展示刺客的狡黠,不计代价、不择手段地应对敌人,这种做法本身也源于敌人。
通过言语来祈求对方放过,是一件尴尬的事,破坏了那种戏谑离奇的体验。把祈求说出口是难堪的,靠行动来求饶、暗算,却打开了回旋的余地。
毕竟,“战士们不求言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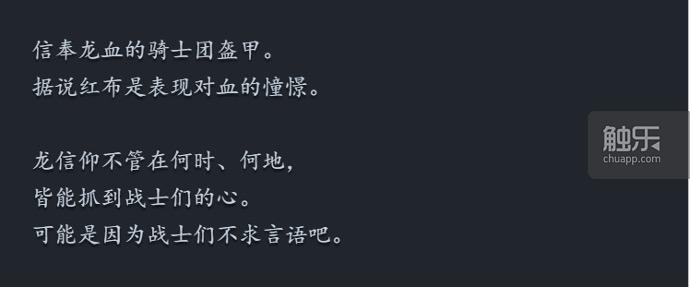
如果说“黑暗之魂”系列察觉到了沉默的价值,那么有一款游戏非常可惜地放弃了这一体验——《人类:一败涂地》。
游戏的原名是“Human Fall Flat”,更直接的翻译是“人类大摔一跤”。标题将剧情说得明明白白——你扮演的是一个浑身疲软的白色小人,从天而降,摔倒在悬置于天空中的奇怪空间里。这里有矿山、城池、别墅以及巨大空旷的洞穴等等。
白色小人因为摔了一大跤而奄奄一息、行动迟缓。只能像婴儿学步一样蹒跚行走、跌跌撞撞、每一次跳跃都可能摔倒在地,即使是伸手触摸门把这样的简单动作,都需要反复协调。

最初遇见这个游戏,我觉得它有种魔力。里面的互动机制无一不呈现出稚童的风格,背后的玩家似乎也受到了感染。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玩家之间(大多数都是智力正常的成年人)不是在通力攻克谜题,而是在相互拉扯、捉住另一个人的耳朵或屁股、带着他在草地上蹦上蹿下,两具稚嫩扭曲的小身体推来打去,跳着没有意义的圈圈舞,却显得十分可爱,这样就能让人玩上很久很久。
假设你带上半生不熟的朋友来玩这个游戏,你们就可以相互解构对方一贯的正经或害羞——我一直想带喜欢的女孩子玩这款游戏,我可以揪住她的耳朵扯来扯去,她还会觉得这很可爱。除了哈哈大笑,我绝对不会说什么废话来破坏这个氛围。

在这款游戏里,我经历了一次让我困惑至今的奇妙体验,几乎让我怀疑,这款游戏的环境和音效设计对于人的心理有催眠般的魔力。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打开一局游戏,我从天空中摔下来,立刻看到有个队友正在操作一架投石机。我当时满心想着要捣捣乱,于是一把拉住他的手往悬崖边冲去,准备带着他一跃而下。
另一个人发现事情不对劲,立刻跑过来抓住我们俩。3个人扭成一团,艰难地朝悬崖边移动。由于我们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外表,经过一段时间胡蹦乱跳,已经无法区分谁是谁,谁在把谁拉向悬崖,谁又在拯救谁。
很快我就发现,虽然我在挣扎中放弃了跳崖的努力,但始终存在着一个用力的人,他拉着我们向悬崖跳去。也就是说,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突然变换了。我们3个人中有两人一齐往下跌去,其中就包括我——不过,就在我即将跌下悬崖之前,第三个人抓住了我的手。
我夹在中间,施以援手者趴在地上抓着我的右手,另一个人抓着我的脚来回飘荡。无论我如何摁手柄,我都无法支撑自己再爬上去,事情非常清楚,救人者必须学会放手,让我俩跌下去——反正,不会出人命。反正,掉下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会重新从天空中坠落到此处,继续参与这场荒唐的游戏。
过了一会儿,抓住我脚的那个人主动松手,掉了下去。而我无法松手——因为我根本没有去“抓住”什么,只有救援者抓住了我。

那个试图拯救我的人,也许正是我最初拉下水的那个,执拗地抓住我的上臂,坚决不肯松手。不论我怎样挣扎,他都不准备放开。我用身体的剧烈抽搐晃动表示抗议,但他拱起幼小脆弱的脊背,艰难无比地向后移动,与我各自卡在无法动弹的窘境里。
有很长一阵子,我完全放弃了抵抗,任凭他抓着我,度过了一段漫长、沉默而尴尬的时间。我没有刻意去计时,但我估计应该20分钟,整个过程,我就那么待着,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大脑一片空白。其他人几乎都离开了,进入下一个关卡区域。而我们,一个抓住地面,一个踩着天空,在沉默中完成一场不可能完成,也绝对没有必要的拯救。那个荒谬的情境像一幅画定格在屏幕之中,完全自成一体。
时间一分一秒地浪费掉,我握着手柄,对这一处境感到有些绝望。从现实的逻辑来说,他的放弃即是我的得救,我要回到地面就不得不坠落。面对他的执拗,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我退出游戏,重新载入。
如此简单的事,在当时却似乎无法做到。因为我代入了进去。我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小孩子,我那么幼小,甚至还没有学会好好走路。我还没有道德观念,所以拉着人家跳楼。他也是个纯洁无瑕的小孩子,他那么善良,即使我伤害了他,他也会帮助我——即使现实的逻辑另有想法,他仍然不会松手,相比现实,主观更重要。这也是一种孩子气的体现。
最后是这样解决的——我也是由此才发现,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聊天的——呵呵,在我的左下角,突然出现了一个方框,一个人用鲜红的字体说:“你俩是有什么神经吧?啊?还玩不玩了。”
我目瞪口呆,愣了好一会儿。我完全出戏了。然后,我打开手机搜索《人类:一败涂地》怎么聊天。
“那个……”我按了T键开始打字,“你还是松开吧。我爬不上来。”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松开了手。随着我的坠落,一些事情改变了。从此,这个游戏在我心中的地位下降了许多。在我不知道存在聊天机制的时候,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催眠。通过代入进摇摇晃晃的人偶,我似乎可以重新体会到生命初始那种茫然的嬉游……关键在于保持沉默,身心投入。一旦默契被打破,开始用上成年人的语言,它就变成了另一个游戏——一个可爱的假面舞会,而不是一次溯源之旅。

关于沟通的游戏机制,我想到的是小孩子和他们的游戏。
在他们那种“Make the world your toys”的天赋影响下,语言本身也是玩具,连口水都能用来嬉戏。比如,他们总是重复地说一句话,像游戏里的魔法师唱诵咒语,试图用言语改变世界。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儿童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操练——操练他对世界的影响,比如建起又推倒积木。尼采的“权力意志”正是在这时生根发芽的。通过这种操练,我们明确自己的主体性和世界的客体性。在更高级的阶段,当我们适应了身体,便开始使用语言,藉由影响社会关系对世界施加间接的影响。
“要买要买要买要买要买要买要买。”
这一切,说是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只是,人越是成长,这套规则就越是复杂。最后,它会变成一场机制高度复杂的大型文字冒险游戏,你需要读正确的书,你需要见到正确的人,你需要用正确的方式说话。不仅是口头的语言,还要全力运用肢体和表情的副语言,以及在关键时刻准备一整套符号——穿着、头衔、爱好、标签、朋友圈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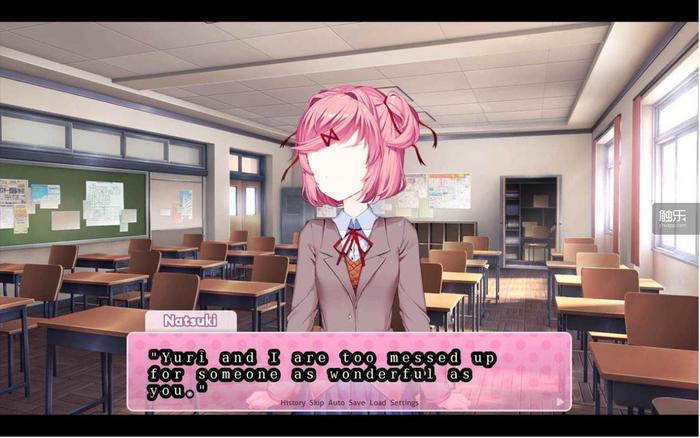
生活的事情如此复杂,我们已经无法将之称为游戏。想想那些无法共鸣的情绪,想想那些无法传达的心意,想想那些误解和相互攻击。
在我们面前,不论“攻略”的是爱情还是事业、梦想,还是一次争论。选项都不是列在眼前任人选择的。正确答案藏得无比艰深,甚至根本丧失了正确的基准。
难怪我们经常讨厌这个“游戏”,难怪我们会回去打造更为简单的版本,难怪我们想要会去游戏里寻找新的沟通方式。
“简单点。”我们的灵魂几乎呻吟着,“简单点。”
我最后想说的是,在这个易于孤独的年代,开口宜单纯、宜友善、宜思无邪。毕竟,在生活里,我们互为彼此的游戏规则。
所以,“简单点。”
* 本文系作者投稿,不代表触乐网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