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之链的力量很弱,因而往往感觉不到,但一当感觉到了,它已是牢不可摧的了。——塞缪尔·约翰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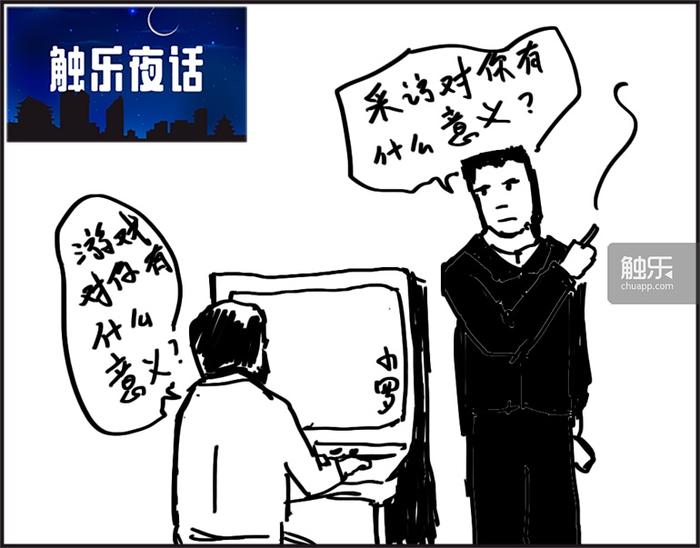
张哥是一位保安,他很偶然的询问了我们公司东南角上摆放的投币游戏机的目录,这事儿被祝佳音老师知道了,他挺着肚子来回搓步,嘴里循环默念着:“看!素材就在身边。”
这就是起因。

抽完从公司顺来的最后一支烟后,我见到了张哥,这时北京的天还泛着煞白,张哥上下打量我,以一个职业性的微笑确认了我的身份。
在11号楼的门襟外,他帮我从大堂里搬来了一张婚宴才会使用的白色布套椅,放在属于他的黑色胶椅旁。
“这个地方行,我一般就在这。”
张哥34岁,祖籍东北吉林,刚入职不久,身上的保安服干净笔直,和这个高档小区很相称。“你说游戏吗?”知道了我的来意,他边说边从裤袋里拿出华为P9,划开解锁递到我面前,上面映着两款手游,《魂斗罗:归来》、《合金弹头OL》,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问:“不玩别的游戏?”
“玩不明白。”
小时候张哥经常往游戏机厅跑,玩不起,只能看着别人玩《拳皇》、《合金弹头》、《三国战记》和《三国志》,张哥比划的这些游戏,仍然记得那时闷热的大厅和晃动的摇杆,总会有人指点江山骂骂咧咧,也有人左右逢源相互夸赞,他觉得光在边上看着就很快乐,那时候的游戏简简单单,血多少就是多少,你有你招我有我招,一招一式逃不过他的眼睛。
“现在的游戏太乱,大家都各玩各的,没意思,耳机一戴,你跟他说话都不带理你的。”
12岁那年张哥和母亲搬到了河北邢台,投奔他的继父。对于生父,他的评价是“没良心”、“一分钱也没往家里交”,母亲没办法,去找爷爷借粮食,爷爷知道了,立刻给粮站打电话把余粮全卖了,最后还是邻居给了10斤米。张哥告诉我:“对他们的恨,岁月洗不掉的。”
继父没有把他当外人,张哥也在那时接触到了小霸王和世嘉MD16位的游戏机,他以“插黄卡”和“插黑卡”来区分,那段时间是美好的,他开始玩FC游戏《三目童子》,名字他已经忘记了,他对我描述是:“有一个三毛知道吗?不对,是一休,脑门上有个眼睛,脑门会发镖。”

通过一些类似的描述,我还知道他玩过《魂斗罗》、《忍者神龟》、《包青天》、《双截龙》、《绿色兵团》、《幽游白书》。 张哥说那会一个游戏机30块,划个价25就成,卡却要15块一张,买不起就只能借,不肯借就等着他玩累的上前玩两把。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7岁,张哥选择了辍学,来北京打工。至于原因,他说:“那时候辍学的人很多,真的。”
其实张哥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小他13岁,见到我一直沉默,他缓缓的补充道:“继父,妹妹,我那时压力很大。”
张哥讨厌现在的游戏,讨厌到不愿多提,他觉得这些游戏除了让你掏钱,就没什么可玩的。
《王者荣耀》是他现在唯一能记住名字的游戏,同事们经常捧着手机玩,但他不喜欢,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上来,只是说“没意思。”
“为什么觉得没意思?能具体点吗?”
“就是没意思,我真的有玩过!”或许是源于我的追问,他不太开心,从我手里夺回了他的手机。
这使我有些苦恼,张哥身上并没有太多在游戏上可以发掘的地方,他的讨厌和喜欢都没有具体的原因,仅仅是直观的好恶,如果要硬套一个理由的话,只能说是情怀了。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我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
为了缓和气氛,我问他有没有尝试过一些端游或者单机游戏,张哥不明白我的意思,用他的方式回答了我。
“现在的钱很黏,我才不会给它。”对张哥而言,游戏这个词,永远定格在了17岁。
初到北京时,张哥在一个尼龙塑料厂用车床加工尼龙布、尼龙板、尼龙套。每天能挣19.9,一个月下来600块,用他的话说管吃管住很知足。后来在大兴根据地,张哥养了一年的海鲜,除了鱼的种类外他并不愿意多讲,这次创业看来赔了钱,因为他的下一份工作是酒店厨房的配菜员。在这里,他认识了小李,小李是厨房的传菜生,每次张哥把师傅炒好的菜配好辅料,交给小李,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
“就是他,骗我进传销。”
“传销?”
张哥看到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笑着说:“对啊,骑着马扛着扁担被忽悠进去了。”
从酒店“下岗”后,张哥待在北京待业,小李给他打了三次电话,前两次都是不痛不痒的问候,第三次便邀约他到河南三门峡,告诉他这边有个“红玫瑰大酒店”,待遇好而且工资高,让他过来。张哥说他重朋友讲情义,没多想就买了去三门峡的火车票。
一到那里,朋友便带他住进的酒店,同时介绍一个陈姓老板给他认识;第二天,陈老板便邀约他去“听课”。
张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说话客客气气,一见面就点头哈腰的自我介绍,鞋子在角落里整整齐齐的摆了一溜,“你刷牙有人给你挤牙膏,喝水,有人给你递水。“那个陈姓的老板甚至会在晚上为你洗脚。”张哥讲完笑得直摇头,说这么多人对他好自己还挺高兴的。
张哥说他当时就知道自己进了传销,但他本来就没有其他选择,而且从没人对他如此好过,于是张哥很安分的在这里听了三天课,“他们跟我讲娃哈哈,成本四毛钱,到消费者手里1块钱,其中的6毛哪去了?6毛是服务费,我们就是这个业务员。” 每天听完课他会问你:“咱们挣的是什么钱。”,张哥说人民币,他们说你没听懂,继续听。
“实际上就是要你说出挣的是那6毛钱,这样你就合格了。”
“他们很爱讲故事”这是张哥对传销的评价,课上到第四天,张哥就已经厌烦了,他找来小李,质问他酒店在哪里,骂小李是个骗子,提出要离开。小李也没有着急,带着他去见各地的“领导”,张哥说这个网很大,在当时到处都是,他沿着三门峡周边见了不下7、8个“领导”。
第一个“领导”一上来就跟他讲了大黄狗的故事,说有个富翁要出去参加宴会,将小孩留在家里,富翁让大黄狗守着小孩,后院里枯井里住着一条蟒蛇,它曾小孩在后院玩耍突然袭击了他,大黄狗奋力抵抗咬死了蟒蛇,救下了被吓晕的孩子,等富翁回家,看到满身是血的大黄狗和倒在地上的孩子,认定大黄狗袭击了小孩,直接掏出枪来把它射死,大黄狗死前留下悲伤的眼泪。这个“领导”讲完拍拍桌子,指着张哥说:“你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
我问道:“所以你被洗脑了?”
“没有!我只是注重朋友情谊,才帮他的。”
就这样,他在这里待了半年时间,张哥可能看出我的怀疑,开始为我梳理里面的套路,来证明他确实没有被洗脑。
他说这里头有三误(雾、悟),一是误会你的介绍人,他一没骗你钱二没骗你色,就一张火车票,钱还是给铁道部的。
二是云里雾里,这个课你听不懂,你就得串寝学习问“领导”,而不是去随便怀疑,五个级别的“领导”,一个一个问过去,再去别的窝点取经, “正面东西反面看,反面东西扩大看。”这话他记得最深,觉得还挺有用的。
三是恍然大悟,选择一家公司一是好处,二是制度,一次性投资终生受益;你再找人一起投资,就有了团队,你也晋升了。一个老太太,C级别,大字不识一个,三个月做到A级别,天天吃住酒店,公司每天给他500块必须花掉。“50斤的大耗子尾巴有三米长!尾巴是什么,就是你的下线团队,稀里糊涂干,半年回头看,一看后面跟着一大片。”

张哥显然对自己的叙述很满意,咽了口吐沫,掏出一包软盒的白沙,自己点了一根说:“这三套下来,人家问你,还走吗,你说不走了。”他接着说: “我在一个地方,无论龙潭虎穴,我就像看看他是干什么的。年轻人喜欢神秘感,我当时才20岁,就算失败了我还能爬起来。”
我问道:“现在还会有这种心态吗?”
“现在没有这个劲了,但现在我跟你说只要是合法的东西我就敢干。”
张哥说他保安这份工作不会长干,等过个几月,就去做电话销售,那东西来钱快。
张哥认识不少楼里做电销、贷款的人,经常在一起聊天抽烟,他们就想拉着张哥一起干,但他有“前科”,有点怕这种事情。他觉得现在慢慢了解了一些,也是差不多的套路,“给你一个400开头的号码,给人打电话就行,能联系上一个来公司就有提成,来了之后交给经理,自己也不用管。”张哥想再干一段时间,存点钱,就去一个电销公司上班。
“你不能打无准备的杖,像赶跑日本人的薛岳将军,为什么别人都守不住,就他守住了长沙,因为他有准备,现在先挣几个钱,没钱不行,不然怎么有收益。”
看到我似懂非懂的样子,他似乎觉得面对一个游戏媒体,说得有些远了,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张哥不怎么回河北,对他来说,家的概念太含糊,直到他2008年认识了自己的妻子,6月份认识,7月份回家,8月份就订了婚,父母因为女方有支气管扩,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张哥不管这些,坚持要娶,他对我说:“我很珍惜她,我走过的路让我知道能有一个信任的人不容易。”
现在这份工作工资4000元,去掉吃喝,还能剩下2000元。这个数字对于有妻子、女儿的张哥而言显然不能再像20岁时知足了,他说一切都是为了他们。
张哥指了指绿化带里的树,树叶被北京的北风吹得来回摇曳,他说他是容易被别人左右的人,就跟这叶子一样没有主张。
对于这突然冒出来的话让我不知道怎么往下接,只好跟他就这样坐着,看着风的表演。
“他们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察言观色,说话。”
“他们?”
张哥没说话,踩灭了扔在地上的烟头。
和张哥在一起聊天的这段时间,我问了两次:游戏对你有何意义。
第一次张哥只说了一个字:“爽!”
这个太过敷衍的回答显然不能满足我,我一直希望将话题引到童年和情怀,但我的计策落空了,从一开始,张哥就没打算去谈游戏的话题,直到采访的结束,出于习惯我又问他一遍。
他很少见的压低了声线对我说:“只是玩顺手,习惯了。”
在地铁站门口,一位小女孩坐在一辆未开锁的共享单车上,靠着栅栏练习着平衡,我点燃了张哥临别时给我的最后一根烟,心里想着末班地铁的时间。小女孩在单车上不住的摇曳,最终完全倾斜在栅栏上,显然她也被这个突然的停顿逗乐了,耻笑着自己的平衡性。
就在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张哥似乎从开始就一直在用传销式的口吻在与我聊天,这一点,我当时没有注意到,张哥也没有,又或者说,这只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熟悉驱使形成的禁锢框架。
“只是玩顺手,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