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们一切都好,他们只是需要被理解。”——丹娜·博伊德
“我想找个CP,最好不超过14岁,愿意发照片的优先。”
如今,许多未成年人正尝试着在网络和电子游戏中寻找情感支持,他们管这叫“处CP”或“处关系”。处CP有许多途径,有专属的“××游戏找CP”贴吧,也有相应的QQ群,更直接的途径是在游戏里边玩边找。
“CP”已经变成了青少年亚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源自英文中的“Couple”(夫妻)或“Coupling”(配对)一词,起初在追星人群中流行,但如今,它可能是一种只存在于网络之中的复杂而脆弱的情感联结,包含某种心照不宣的暧昧、半拒半迎的闪躲和欲说还休的试探。是一种一对一的、具有排他性质的情感关系。它有爱情的性质,但又并不是爱情。
我们和想要“处CP”的青少年们谈了谈,也对一些家长和老师进行了采访。为了保护青少年受访者的隐私,我们没有选择他们的家长,而是另外寻找拥有适龄子女的父母作为采访对象。我们不想成为“孩子们遭遇网络侵害”或是“青少年网络早恋”这类标准恐怖故事的传播者,事实上,这些故事的确存在,但它们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
当父母和老师们还在用羞耻和遮掩的态度来谈论青少年话题时,孩子们自己要坦荡得多。我在和青少年们交谈时,他们并不觉得在网上“谈CP”有什么羞耻之处,这与他们的父母辈刚好相反,父母们在谈起“早恋”时,更倾向于快速引开话题,并且尝试说服我,“我的孩子还小,并不考虑这些”。
“他才14岁,一看动画片就来劲,肯定不会早恋。”天空的爸爸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可能并不清楚,在网络上找CP的孩子们中,有许多人比他的儿子还要小得多。对部分女生而言,“14岁男孩”已经不再纳入考虑范围,她们只想要“11到13岁”的同龄人。有人自己找到了CP,还会当起月老,牵拉红线,试图帮身边朋友“脱单”。

可乐今年17岁,北辰13岁,两人都在互联网上公开找CP。这不是个例,随便哪个交友论坛里都有11到17岁的男孩女孩发出自己的照片,寻找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CP。在这个语境下,“CP”指的其实是“一对一的聊天对象”。
这没什么吃惊的。当青春期来临,男孩和女孩都会对异性(有时候是同性)产生兴趣。这些事或许不会被放在阳光之下谈论,但它们在“没有家长存在的地方”差不多也是公开的秘密。
青少年们有了隐私意识的萌芽。找CP时,一部分人会公开留下联系方式,但更多的人只在游戏或论坛内表达自己想要CP的意愿,然后通过私聊确认,双方满意后才交换QQ或微信号。有的时候,孩子们由于缺少经验,会在网络世界里无意识地暴露信息。有一次,一个女孩在论坛求CP时发出了自己的照片,她模糊了自己的脸,却没有抹去自己身上的校服和身后的横幅文字。
孩子们想要找CP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人告诉我是因为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还有人的理由是“闺蜜都有,我也要有”。有人想要游戏中的虚拟货币,也有人出于对“言情小说”中恋爱的向往。
成年人总是觉得,儿童(及早期青少年)和性完全无关,当孩子长成大人,他们就会遗忘自己童年的经历,假装自己的成长历程单纯无瑕。但事实上,自电视诞生以来,儿童就有了和成人同等程度地接触信息的能力。古典时代,知识通过文字传播,识字和写字技能需要通过教育的途径获得,这天然地隔离了儿童与成人的世界。但在互联网语境下,青少年只需要很少的知识就能够进行自由检索,这意味着与性有关的刺激变得唾手可得,且更为隐蔽。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孩子们不去顺应自己的天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不存在围栏,一切与性有关的图片和视频都是易得的。我伪装成一位15岁的少女进入社交App里查探,不出5分钟,就有人主动搭讪我:“文吗?”
“文”大概是“文爱”的意思,即“交流双方用文字模拟性刺激”的简称。在这里,想要寻求到一场不具名的艳遇轻松又容易,并没人在乎你成没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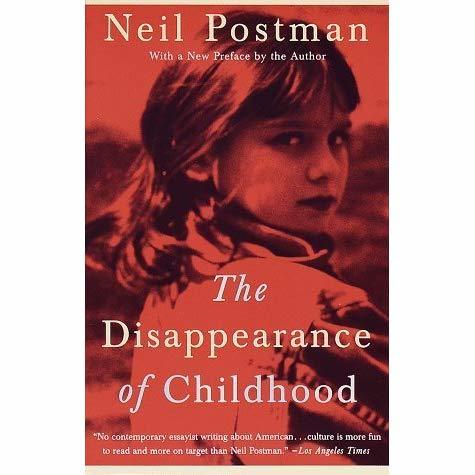
网络活动好比一场丛林探险。在电子游戏中,青少年们进行着关于性的探索与认知。电子游戏在青少年自我认知探索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虚拟游戏非现实的特性使得孩子们能在探索性与爱情的时候建立起心理安全网,他们关于“爱”和“相处”的知识在游戏中潜移默化地习得,这里面有时也包括了“如何应对危险”。
当然,在现实中真真切切地谈一场恋爱或许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但在前者几乎一定会受到父母、老师的密切关注和频繁干涉的前提下,青少年转向游戏去寻求情感支持是更隐蔽也更简便的做法。
今年13岁的初一女孩月亮在QQ聊天和手机游戏中发展出了超过10个“前男友”,她拥有大约200个快手粉丝,在QQ空间里,她的每一条状态都有近千点赞。在父母的视线之外,许多像月亮一样的青少年相互隐蔽地交流着,网络世界平行叠加于规律的校园生活之上,青少年们活在双重世界的交错之中。
月亮的父母对月亮的网络经历一无所知。月亮的手机每天晚上都会被父亲收走,放在自己的房间,他就像是公元前的波斯国王,对发生在眼前的暴乱毫不知情——公元前440年,希腊人Histiaeus剃光了奴隶的头发,把信息写在奴隶的头皮上,当头发重新长出,信息就会被隐匿住。没有人想到去剪光奴隶的头发,信息大摇大摆地在想要捕捉到它的人手中溜了过去,这是现代隐写术的起源。

我并不认为大多数青少年懂得信息传递法则,但作为群体的他们,几乎是毫无疑问地在与家长、老师等权威对抗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内部交流方法。“隐写”不是数字时代的专利,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期,青少年们通过墙面涂鸦、纸条留言来相互交流,如果“外行人”不知道信息存放在哪儿,他就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青年人们谈话的内容。
这套方式是潜意识化的、在群体内部不言自明的隐藏规则,当我尝试以一个外来者的姿态采访并进行信息收集时,每次都被立刻认出,而孩子们也多半会本能式地采取抗拒姿态。
我用过很多种开场方式,从“我是触乐网编辑,方便聊一聊吗?”“您好,请问您要找CP吗,想听听您的故事。”到简单直白的“找CP吗?”“能聊天吗?”,有时,对方会回复一个“嗯”字就再无下文,有时会骂我几句,叫我立即滚开,更多的时候,我的好友申请和对话请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有一次,我试图采访一个孩子。他对我说:“吾疑汝驭车且狂飙之,奈吾无据以示众。”这句话的意思——换成普通话——就是“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我没有证据”。我礼貌地请求他使用我能听得懂的话回答,他回应了5个字:“浪费我时间。”
但好在有愿意接受采访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手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在父母的管控之中。一个典型的范例是这样的:青少年们每周一至周六在学校上课,周日下午或晚上得到手机,并且能够在父母的注视之下玩上一会。与此同时,父母们并不了解青少年网络世界的玩法与规则,在他们的视角中,孩子只是坐在沙发里或躺在卧室床上和手机待了一段时间。
互联网的意义之一在于,物理身体不再是人的唯一存在形式。社交媒体、游戏账号等载体创造了新的“人”的存在依托。电子游戏构建了新的世界。对许多60、70后的父母辈而言,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对00年上下出生的青少年们,它简直如同吃饭喝水一般自然。
即使青少年们在父母眼前谈论网络世界的图景,父母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没有多少70年代出生的父母辈知道“CP”或“CGX”(处关系)、“扩列”(交友)等词的真正含义。
“我认为孩子们发明了一整套间谍技术和特工语言。”铭铭的母亲告诉我,“我从他那里听到过一些词,像是‘盘他’,还有些我忘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显然,“盘”这个字在70年代出生的她和00年后出生的儿子眼中,分别存在两种并不相同的含义。
1973年,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正式提出编码解码理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传播者将信息进行编码,由于接收者的社会背景、思考方向不同,对同一信息会有不同方式的解码。这意味着即使两位解码者阅读了一模一样的编码信息,他们也很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每位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状况颇为自信,他们并不知道青少年群体自发形成的对抗策略。一些青少年为自己的编码信息想出了逻辑自洽的解释方法,在00后的网络聚居区里,可以看到青少年们自发向同辈们传授心得——当自己的“编码”被发现时,如何用不会引起家长恐慌的办法编造出一套新解释。当家长们自豪于孩子对自己“什么都说”时,也很难想到这也是青少年们的策略之一。孩子们会主动吐露一些在家长视线范围之外发生的事情,以此来获取信任和隐瞒更深层次的信息。
铭铭(13岁)的母亲向我讲述了一个叛逆儿子与心碎母亲的故事。
在她的故事里,儿子和她几乎每一天都在争吵,儿子对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下意识地进行反驳,而她也将会用一种更为严厉的姿态维持住家长的威严。和我交谈的前一天,她和儿子为了汉字“藤”的写法争得面红耳赤,铭铭把藤字下方的“水”写得模糊了一些,妈妈让他重新写一遍。“可我考试的时候不会这么写的!”面对大声争辩的儿子,母亲选择以更强硬的姿态对抗。
孩子们生活在重复性的规律作息与集体组织活动中,游戏可能是唯一的逃离渠道。14岁的天空每天早上6:20起床,晚上10:00写完作业,周六日还要参加兴趣活动和课外班,每周,他有一小时时间可以用来玩游戏。12岁的小涵每天只有临睡前的半小时用来娱乐,爸爸会和他一起,玩一些他喜欢的电子游戏。同样12岁的筱筱生活则要宽松一些,但她的妈妈每次看到孩子玩游戏都要劝阻一番。

我不知道,他们的“叛逆”是否是对成年人无休无止关注的一种反抗。“社交媒体”或“电子游戏”或许是平淡生活中的唯一出口——他们在这里获得了自主与权力,以及不受管控的一小段时间。
很少有人会在游戏聊天中提起自己的父母,即使有,父母也经常扮演着反面角色。在青少年的视角里,父母代表着“高压”“控制”;在父母眼中,孩子则是“叛逆”“沉默”“不知道在想什么”。在父母辈的诉说中,青少年们展现出的形象是低龄化的、宛如白纸一般,沉默地听从着父母的指令,而在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中,青少年们完全换了一番模样。
“我想在游戏里找个爸爸。”一个女孩在游戏中的留言板写道。虽然她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玩的游戏中,那些“求女儿”的留言意味着什么。
父母们也不理解孩子的感受。那天,铭铭妈妈对我说,有一次铭铭爸爸出差,“只有我们两个在家,那段时间工作很忙,他干什么我都不说他”。她和儿子在家里和平相处了一天,铭铭在晚上告诉她:“我感觉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家,也挺好的。”
我问她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吗?她以沉默作答。
与其说科学技术在创造新的社会问题,不如说,它们是现实生活的放大器,让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明显。
在青春期,孩子们会开始渴望扮演社会角色,他们希望取得像成人一样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CP”和“过家家”一样,是儿童对成人世界无意识的拟态与攀仿。电子游戏世界给予青少年伪装扮演的机会,他们长期生活在成人的保护(也是限制)之下,这些以爱为名的关注和注视——有时候也阻挡了他们前往更广阔的世界。许多人都听过“最后一根稻草压死骆驼”的故事,一根稻草并不可能杀死骆驼,儿童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变为成人,他们会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尝试、摸索、学习,寻找和世界沟通的正确方式。
当我们提起“青少年在游戏中尝试组建CP”时,这件事很容易和另外几个词在读者脑海中组合在一起,例如“早恋”“游戏成瘾”“青春期叛逆”等。然而,这些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逻辑并非如此。
“孩子不会永远只是孩子,他们是未来世界的成人。”省级骨干教师姚老师对我说,“当你看着你的孩子的时候,你需要想一想,几年之后他是社会上的成年人,他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孩子们把自己想象为成人世界的一员——在他们关于“CP”话题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想象的原型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恋爱。没有人去教过孩子们,青春期和异性(或同性)相处的正确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只能从影视作品、电子游戏中获取想象的养分,而这些作品默认的观众本来是成年人。
卡迪夫大学的Netta Weinstein博士认为,游戏过度本质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需求不满有关,她说,游戏是一种替代性行为,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不快乐的心理补偿。圣文德大学心理学教授Kimberly Young则认为:“当有人花了太多时间玩游戏时,应该检查是什么样的情感动机促使他这样做,并想办法寻求相应的情感满足。”
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互联网上遭到性掠食的孩子们,也就是家长们通常最担心的那种情形的孩子们中,许多人曾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并不美好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暴力、性虐待、冷暴力、校园欺凌、父母离异、情感虐待等等。拥有糟糕经历的孩子们在网络上接受性引诱的概率大约是普通孩子的2到2.5倍,同样的相关性也在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强暴案例中体现。
在“和网络上认识的年长先生(女士)外出约会”的孩子们中,大多数人知道对方的真实年龄,也知道自己前去会发生什么。他们不是茫然无知的小白兔,在他们眼里,自己的行为“全然出于自愿”——即使在法律上他们没有“自愿”的能力。
我不想在这里继续讲述青少年在网上遭受蒙骗,不幸被性侵犯的故事,它们的确存在,有心的读者能够在网络上发现无数个这样的故事,但真正的问题是,类似的故事在现实中同样上演着——去掉“网络”和“游戏”,故事的本质依然没变。“游戏成瘾”和“社交网络”掩盖了一些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关于这些孩子为什么“自愿”,和孩子们逃离现实的真相。
责备青少年们总是容易的,他们缺少足够的话语权,当孩子们想要站出来发声时,大多需要一个“成年人”式的传播渠道。当成年人替青少年发声时,所有的语言都会经过成人思维和成人式话语体系的转换——本文亦不例外。怪罪父母也没有多困难,70前后出生的人们不常使用网络,许多人活在媒体营造的思维定式之中,稍有教育学或心理学背景知识就能看出,不少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沟通存在极大问题,并且父母方负有更多责任——但这本不是他们的原意。代际冲突中,爱与权力一体两面,相伴而生。
“教育”不是一道拥有正确答案的单项选择题,世界上也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当父母们尝试用他们童年记忆中的方式去养育孩子时,总容易忽视时代、社会的变迁,也容易忘记当他们身为孩子时,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在儿童与成人天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双方“换位思考”是件挺难的事儿,这种语境里,呼吁“家长和孩子相互理解、平等沟通”是句正确但空洞的废话,但事情归根结底似乎也只能这么解决。
在一个复杂的困境中,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方是种轻易但不负责任的做法。寻找情感慰藉的青少年、提供娱乐的电子游戏、焦虑的父母们……复杂的社会博弈背后,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没做错,在以自身为逻辑基点的视角中,任一方都能以受害者的方式进行叙事,孩子们看到的是高压控制的父母,父母们眼中则是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对孩子“成才”的无尽焦虑,电子游戏更多想的是自身运营和生存。
一切以爱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