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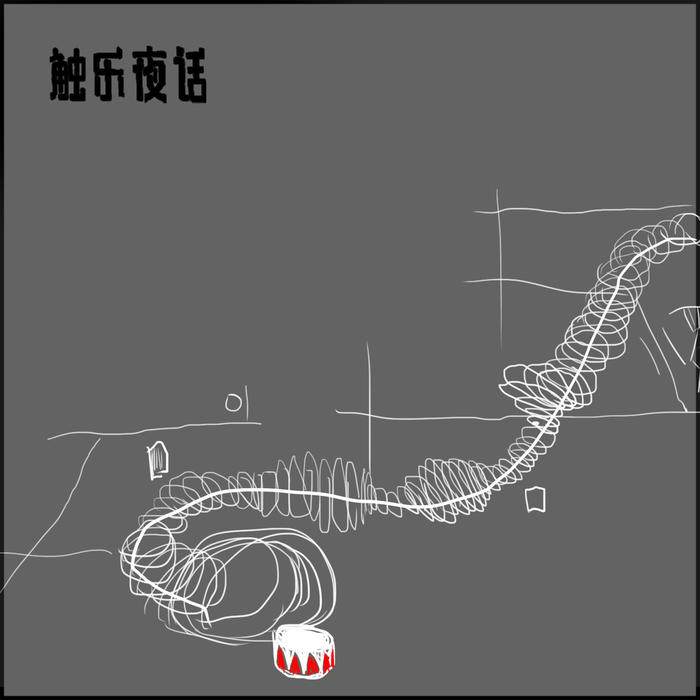
有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这样的片段:一个人在某个必然的瞬间被生活推着,担起责任感,她(他)不假思索地承担了,日后的悲剧与困苦就此埋下伏笔。
为这样的片段忧虑、紧张的,不仅有我,还有很多很多人。我很肯定其中包括《肯塔基零号国道》的开发者们。
一直以来,《肯塔基零号国道》对我的意义像是个风向标:我上大学时就听过这款游戏,被那些夸耀它的玩家所吸引,为了成为这样有品味、懂得如何最大程度地品尝一款游戏的“理想玩家”而去玩游戏。
实际上,当时我并不理解《肯塔基零号国道》在表达什么。游戏中没有谜题,对白和演出却模糊得像谜题,还有角色慢得让人心碎的脚步,都无不在告诉我,那时的我并不属于它。
于是我像很多人一样,尝试从更加形而上的角度来解读这款游戏,我会说我很喜欢马群挡住去路的片段,或者去想象那像是卡尔维诺本人执笔一样、可以被反复解读的仙都,但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款游戏。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过着我所追寻的自由的生活,我不想受到任何束缚,我迅速和很多人亲密起来,又很快和他们断开联系。我离开自己的家,又怀着渴望进入同龄朋友不屑一顾的家庭,和他们的父母熟悉起来,又果断离开。我不喜欢和我同龄的人,我更喜欢比我大几岁到十几岁的人。
我很失落,但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我害怕开头的那个片段,我逃避责任感,自私且自我——我知道这点,所以没什么底气地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
处于这样的生活中,我有时候会想起《肯塔基零号国道》里的回声河:我要越过河流,来抵达意欲前往的目的地,却始终让自己浸泡在河中,无期限地握着电话,倾听里面永远不会停止的回声。
也就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肯塔基零号国道》所蕴含的究竟是什么。它既不是纯形而上的一堆譬喻,也不是纯实在的一个故事,它提供的是一种叙事。让玩家得以有机会,通过游戏中的语言,来表达或者说审视自己。这个过程轻快、不沉重,还很美。
我喜欢回声河,我喜欢在林中奔跑,我喜欢会掀开房顶让星光洒在周身的歌喉,就像我尽管此刻心情灰暗,但我还是喜欢自己,我虽然怀疑,但还是认可这个自己。
《肯塔基零号国道》的氛围是失落的,在我看来,这种失落的前提是“自由(往日)不在”。
这次夜话的名字带有《铁皮鼓》。它讲的是3岁的侏儒奥斯卡在拥有了铁皮鼓后拒绝长大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魔幻,就像《肯塔基零号国道》一样。我尤其喜欢这一段:小奥斯卡发誓不再敲鼓后,他长大了,整个故事的魔幻感就此消失殆尽,少年的奥斯卡屈服于魔力。成年后,他开始追逐各种欲望,寻找活着的意义、生活的责任——但那面鼓始终在那儿,等待他敲响,后来他敲响了吗?
我看到他敲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