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总有世间绝景,我愿长为南北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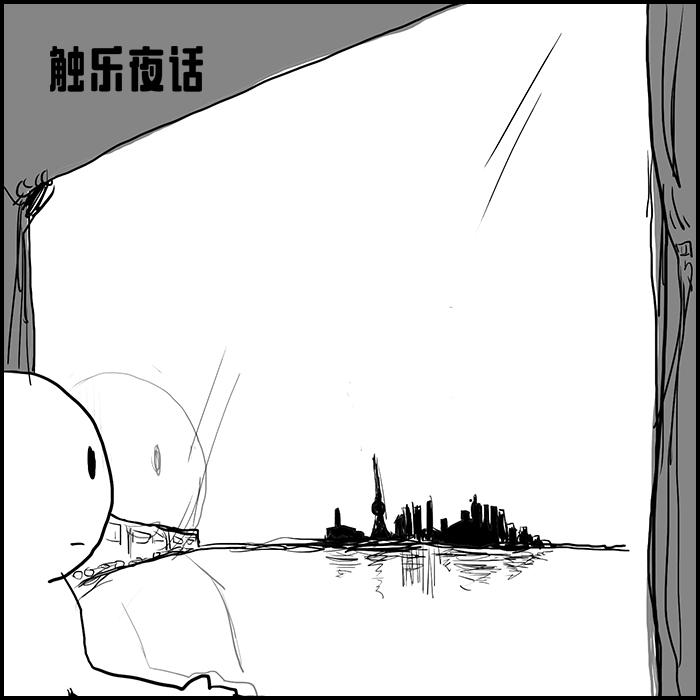
背着沉重的行囊,我从虹桥火车站汹涌的人潮中穿过,寻找一个等待返程列车的去处。
这是我这个月第二次来上海了,一周之后还有第三次。我记得杭州的双层公交车即将停止运营的时候,有好多情侣会一直待在在二层最后排的座位上,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到起点——我现在这种反复横跳的状况有点像那时的他们,只不过高铁似乎永远不会停运,而且我只是一个人。
在双层巴士的二层,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不太刺眼的阳光充满了低矮的车厢,西湖的四季从两侧涌入,成为一片花香和湖光的肆意汪洋。这种体验比它具有特殊含义的编号更让人沉迷其中,恋恋不舍。

这几年来,我好像总是在从北京到上海的路上。每一次我来到这座城市,也总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绝景——除了鳞次栉比的都市和流光溢彩的江滩,还有喜怒哀乐和人间百态。
我想我和上海的因缘是从3年前的上海电影节开始的。为了看一些网络上还没有资源的日本电影(主要是为了中村义洋的《残秽,不可以住的房间》),我在频繁崩溃的抢票软件中左支右绌,买到了五六张电影票,乘着颠簸的T字头火车来到了上海。我已经无法回忆起当时看了哪几部电影,只记得巨幕中的桥本爱美得摄人心魄,以及留下了“粉红少女滤镜完全不适合二阶堂富美”(指《狼少女与黑王子》)的印象。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在微博上一直有交流的N君。她恰好和我看了同一场的《残秽》,在入场时没有遇到,散场前她又提前落跑,留下了一句“老阿姨不好意思见人”的玩笑。不久之后她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不再更新微博,也断了所有的联系。
多年之后我还是会想起这位消失已久的朋友,想起那段一起讨论日本若手的时光。那些互动现在看来也许平平无奇,但是擦肩而过和消失不见让它变得无比珍贵——我是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这种感觉。
电影节的最后一天我错过了末班地铁,路上也没有出租车,我从喜马拉雅中心走到了黄埔江边。凌晨4点的外滩空无一人,在流光溢彩的灯火关闭之后,被夜晚的行船无数次切开的江水得到了短暂的平静。我脚步沉重地走过江堤,却感觉自己在夜色里滑行。

后来则是跑去看十八线女团。难得抽到了票,就不远万里去到那个不大的剧场,因为我在台上看到了星光。后来我发现那些星光不在聚光灯下,也不在麦克风里——所有的美好其实都来源于自己。
那天晚上舞会球下的Disco和告别让我眼眶湿润,如今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幻梦。没有那么真的感情,也没有那么远的宇宙。我不知道闪闪发光的玻璃球带她们去了哪里,但我日夜注视着水星,却看不到人影。
倒是一起喊Call的朋友们的故事会更加有趣。漱之的包被清洁阿姨错当成垃圾丢到了附近小区的垃圾桶里,我们陪着他在黑暗和恶臭中苦苦寻觅。好不容易找到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查看一下身份证和现金,而是掏出了包里刚买的生写到剧场对面的公共厕所里反复清洗——看到此情此景,原本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气都变得甜腻了起来。

这次来上海是在Ti9的前一天,我在Aster战队的基地里见到了BurNIng。显然不太擅长聊天的他用得体的话语回答着我的问题,流露出恰到好处的感情,熟练得让人心疼。没有进入Ti的Aster队员们在屋外打着天梯,没有开灯的房间显得有些沉闷和压抑。
从万众瞩目到被当成笑料,Aster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大半年的连续失败和来自网络的巨大压力看上去正在消磨这些天才选手的意志,不论他们年轻或是不再年轻。基地离梅赛德斯-奔驰中心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竞比赛即将在不远处举行。
我无法揣测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试着不流露出一丝轻蔑,也不表现出一点同情。他们必须靠自己挺过去,也只能靠自己打出来。

告别了炎热的天气与熟悉的吴语,我又一次踏上归途。我呆滞地看着窗外不断延伸的铁轨,回忆着自己与上海的故事和那些早已远去的时光。这些旅行的记忆总能在某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带来足够的食粮,让我能够看到光,看到天亮以后的水远山长。
倘若总有世间绝景,我愿长为南北旅人。